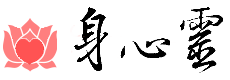何來有我
-佛教禪修指南
Who Is My Self?

A Guide to Buddhist Meditation
The Potthapada Sutta
The Buddha’s Words on Self and Consciousness
Interpreted and Explained
by
Ayya Khema
艾雅 柯瑪 講述
果儒 譯
《布吒婆羅經》是記載佛陀回答布吒婆羅有關自我和意識等問題的開示;此書系作者對《布吒婆羅經》的詮釋和解說。此書對修行的次第和四禪八定也有詳細的說明,是非常好的禪修指南。
目 錄
前言……………………………………………………………3
第一章:修行的起點…………………………………………5
第二章:守護根門:正念與正智……………….……………23
第三章:去除五蓋……………………………………………38
第四章:初禪…………………………………………………53
第五章:二禪和三禪…………………………………………70
第六章:四禪…………………………………………………87
第七章:第五禪和第六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107
第八章:第七禪:無所有處定;第八禪:非想非非想處定;
第九禪:滅盡定:………………………………123
第九章:出離、離慾和四聖諦……………………………137
第十章:貪愛的止息:趣向涅槃……………………………151
第十一章:去除自我的幻象………………………………166
第十二章:哪個是真正的自我……………………………182
第十三章:道及果:修行的目的…………………………200
附錄一:三學、七清淨與十六觀智………………………218
附錄二:布吒婆樓經………………………………………219
附錄二:修習慈心…………………………………………242
作者簡介……………………………………………………244
前 言
當越來越多人開始追求生命的意義時,人類似乎已進入新的歷史。在過去,人們追求幸福的家庭生活、宗教、政治和職業,認為這些可以使生命更圓滿,即使這些願望不會掛在口邊,卻在每個人的心中。
今天,以往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理論早以搖搖欲墜,難以作為有意義的生活的基礎。假如我們認為,只有二十世紀的人類才知道追求生命的意義,當我們讀了《布吒婆樓經》佛陀的開示後,就知道我們錯了。
經中有一位叫布吒婆樓(Potthapada)的外道,向佛陀請教許多有關自我(Self)和意識的問題。佛陀煞費苦心、不厭其煩的為他解說,給他正確的指導,教他如何修行,以證得最圓滿的解脫,這段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對話至今依然中肯貼切。
我們也會讀到布吒婆樓的朋友和夥伴們不同意這些新的想法,並想使他放棄對佛法所產生的興趣,這現象至今依然如此。
我希望藉著對這部經的解說和詮釋,使這部經變得生活化,並為讀者們指出方向,使讀者在修行中發現生命的意義;而所有找到內心的平靜、喜悅和滿足的人,希望他們對世界和平及人類福祉能有所貢獻。
本書內容來自一個為期三週的禪修營中的講座,地點在美國加州,時間是一九九四年五、六月。
由於Gail Gokey和Alicia Yerburgh的慈悲、慷慨和參與,讓我們能讀到這些有助於修行的文章。我個人非常感謝Gail和Alicia的辛勞,也感謝Toni Stevens,他很善巧的安排這次的禪修營;也很感謝Traudel Reiss在電腦方面的幫忙,使編輯及校對得以順利進行;在Tim McNeil幹練的領導下,智慧出版社為本書設計精美的封面, 而我也很高興能名列出版社的作者群之中。
如果本書能使那些修行人對佛法更有信心,更喜歡修行,能獲得更高的內觀智慧,得以觀察究竟實相(absolute truth),那麼所有為本書流過汗水的人都會感到非常欣慰,也會以同樣的方式付出我們的時間和愛。
在修行的過程中,在解脫道上,我們都具有開悟的潛能,願此書成為禪修者的良伴,願正法常住人心。
艾雅、珂瑪 于德國.佛陀精舍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第一章
修行的起點:持戒
上座部佛教以巴利三藏作為佛陀教法的基礎,巴利文是由梵文演變而來的,為佛陀所使用。兩者的不同正如拉丁語與意大利語。在當時,學者們會說梵語,而一般大眾則會說巴利語。佛教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巴利三藏又稱為Tipitaka,Ti是三的意思,pitaka意為籃子。三藏包括律藏(Vinaya),記載比丘及比丘尼的戒律;經藏(Suttas),記載佛陀所說的法;論藏(Abhidhamma,阿毗達摩),是佛教較高深的教理。為甚麼稱為三個籃子呢?因為最初的經文是寫在乾燥的香蕉葉上的。乾的香蕉葉頗為堅實,將經文刻在葉子上,再塗上特製的草莓汁,再將其他部份抹掉,就會留下黑色凹陷的文字。直到今日,斯里蘭卡的某些寺院仍用這種方法來複製經文,當舊的葉子毀壞時,僧眾會把舊的葉子中的經文抄錄在新的葉子上,這些刻有經文的葉子會用很厚的木板放在葉子的上下方,然後綑綁起來。有些施主會用金或銀裝飾的木片,以表示對佛陀的敬意。這些貝葉經並非書本,無法用一隻手拿著,通常這些貝葉經會放在三個籃子裡,以便攜帶,所以巴利三藏又稱為Tipitaka或三個籃子。
此書從開始到結束都在討論一篇英譯的《長部》 (Digha Nikaya)第九經經文。Digha意為長,Nikaya意為部。佛陀入滅多年後,他的開示被結集成五大部類的經典,分別是《中部》(Majjhima Nikaya、《長部》、《增支部》(Anguttara Nikaya)、《相應部》(Samyutta Nikaya)和《小部》(Khuddaka Nikaya) ,不適合歸入前四部的經典,則收入《小部》。
《長部》經文包括整套的修行方法。我們必須知道佛陀在兩個層次說法,一個是相對的層次(relative truth),另一個是絕對的層次(absolute truth)。剛接觸佛法時,我們對絕
對層次的法沒有概念,若碰到絕對層次的法(truth),可能會退縮,因為同一個問題在兩個不同的層次上討論,會有不同的答案。例如,我們聽了一個禪宗的公案後,會茫然不解,不知其所以然,這是因為公案的道理是無法從相對的層次來理解的。記住:在絕對的層次永遠不會有自我,所以公案的道理只有一點,也就是沒有實體,沒有自我。
我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體會這兩個層次的法,以一張桌子和椅子為例,對一般人而言是兩件家具;而對物理學家來說,它們只是由能量所組成的粒子(particle)而已。物理學家下班後回到家,一樣會坐在椅子上和使用桌子。
當佛陀說無一物,沒有自我時,他是在說絕對層次的法,以絕對層次而言,我們每天所面對的世界只是視覺和心理的幻象罷了。佛陀也說相對層次的法,所以佛陀也用「我」、「我的」、「你」等字,他教導與我們有關的事,如業(karma)、心清淨、情緒、身心等。我們必須了解這是兩種不同層次的法,表達的語言因而大不相同。
當我們深入探討這部經時,就會了解絕對層次的法,這點非常重要,因為佛陀告訴我們,一旦我們證悟絕對層次的法,必定可以永遠解脫苦。佛陀所教的法和指導,使我們一步一步的邁向證悟-這是佛陀親自證悟的經驗。
現在的科學越來越能證明這些經驗,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更妙:佛陀所說的法印證了今日的科學。絕大部份的科學家都未證悟,雖然他們知道:一切物質只是聚合又分散的粒子,卻不了解他們也是粒子而已,沒有實體;假如他們把自己也列入觀察的對象中,這些科學家可能很久以前就已經證悟,而且很可能在教導世人如何證悟,而不是在教物理了。
我們也許聽過或讀過這些理論,也頗感興趣,然而如果我們不去實踐,這些道理也就沒有甚麼用處。佛法最大的益處是它的可行性,而解脫道上的每一步都是切實可行的。
我所選的經典是《布吒婆樓經》 ,此經的副題是心識的各種境界(States of Consciousness)。在經中,佛陀對某人說法,並回答他的問題,所以許多佛經都是以人名為經名。此經是佛陀為布吒婆樓所說,故以布吒婆樓為經名。
大部份的佛經以「如是我聞」開始(巴利文是evam me suttam),原因是所有的佛經都是讀誦的。第一次結集經典,是在佛陀入滅後的三個月舉行,參加的全是阿羅漢,誦經的
內容包括:說這部經的地點、有哪些人物在場,以及主要的問答等。這些內容使在場聆聽的僧眾能記住經中的場合,他們同意或不同意這部經的內容,如須更正,僧眾可以建議修改經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給孤獨長者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他第一次聽佛陀說法便皈依佛陀,成為佛弟子,那時由於佛陀和他的弟子們仍是遊方僧,所以他想捐一座寺院給佛陀,他找到一座屬於祇陀太子的芒果園,然而祇陀太子卻拒絕出售,給孤獨長者很有耐心,向祇陀太子請求了許多次,最後太子說,如果給孤獨長者能以金幣覆蓋整座芒果園,他就會賣給他。給孤獨長者命令他的僕傭們運來一箱箱的金幣,想把整座芒果園覆蓋住,金幣用光了,還有一小片土地未舖上金幣,最後太子也把這片土地供養佛陀,所以這座林園稱為祇樹給孤獨園。
給孤獨長者花了三分之一的財產買下這座芒果園,又花了三分之一的財產建造精舍。佛陀在此園中度過了二十五個雨安居。在印度,雨安居指在雨季的三個月,僧尼留在寺院學習和禪修,不外出托缽。雨安居的原因是:在佛陀時代,所有的僧尼都必須托缽,以獲得他們的食物。在雨季,幼小的秧苗種在水中,隱藏在水中,僧尼不小心便把秧苗踩死,因此有農夫向佛陀投訴:僧眾在雨季外出時,經常不慎踐踏農作物。由於有上千位僧尼外出托缽,結果導致農作物欠收,使農夫挨餓,所以佛陀就規定僧眾在雨季時,要在寺院安居,由信眾把食物帶到寺院供養僧眾。雨季安居至今仍被遵守。
時布吒婆樓苦行外道,與外道眾三百人,住末利園中,提陀迦樹(Tinduka)環遶之大講堂。
在佛經中,稱其他宗教的出家人為外道或苦行僧。末利(Mallika)夫人是波斯匿王(Pasenadi)的王后,她是佛陀虔誠的信徒,也是外道的施主。
爾時世尊,清旦,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然於其時,世尊念言:於舍衛城遊行乞食,為時尚早,寧可往訪末利園中提陀迦樹環遶之大講堂。
由於為時尚早,所以佛陀未去舍衛城(Savatthi)托缽。經中經常提到舍衛城,因為給孤獨長者布施的林園就在舍衛城附近。雖然佛陀只在印度北部教化,但佛法卻從此地弘揚到世界各地。
時布吒婆樓苦行外道與諸多侍眾共坐一處,大聲喧嚷,互相詈罵,耽於種種無益議論,即論王、論盜、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論飲、論衣、論床、論鬘、論香、論親戚、論乘具、論部落、論村莊、論都市、論鄉間、論婦女、論勇士、論市街、論瑣事、論亡靈、論餘諸雜事、論水陸起源,及論斯有斯無等。
經中一開始,一群以布吒婆樓為首的外道正在閒談,談論一些俗事及無益修行的話題。佛陀認為我們應該避免這些閒談,因為談論這些,不但會引起紛爭,還會擾亂內心,會引起慾望、情慾等不善心所,也會產生執著和自我認同。即使今日,在所謂的第三世界,井邊仍是重要的聚會場所,因為許多地方沒有自來水,所以附近的居民在井邊閒談,並交換最新消息,這些閒談經常會造成中傷、毀謗。這種閒談是佛陀禁止的,因為這些言論無法產生智慧,也無法使我們的心轉向修行、解脫。
爾時,布吒婆樓苦行外道遙見世尊,自彼方來,即令其眾,靜默勿嘩,曰:「諸君,肅靜勿聲。沙門瞿曇來矣。彼愛沈默,彼長老並讚嘆沈默,若知吾等會眾沈默,當覺此行不虛也。」彼等苦行外道,聞是言已,眾皆沈默。
布吒婆樓看到佛陀走近時,以歡喜的心向佛陀問好,在下一段經文中,可以看出布吒婆樓是多麼高興能見到世尊。
布吒婆樓語世尊曰:「善來世尊,吾等歡迎世尊。世尊久未來此。請坐世尊。此座之設,為世尊也。」
世尊就所設座而坐,布吒婆樓別取低座,坐於一旁。世尊告布吒婆樓曰:「布吒婆樓,汝等集此,以何因緣,為何論議?而汝等論議何故中止耶?」
佛陀想知道他們的問題所在,好幫他們解決疑難。
布吒婆樓聞是言已,答世尊曰:「世尊,吾等集此,所欲論者,可暫置之,因此等言論,世尊日後易得聞也。」
布吒婆樓不想告訴佛陀他們在談論甚麼,因為他有更重要的問題要問佛陀。
世尊,邇來頗有外道沙門、婆羅門,集此講堂,就「增上想滅」發出議論,曰:「增上想滅,云何可至耶?」
識(想)最究竟的滅盡境界(增上想滅),有時指第九禪(jhana)的境界,也稱為滅受想定,在這個境界中,受和想(perception)的作用都會停止。我們將在稍後的篇章中討論各種禪定。布吒婆羅所提的問題-滅盡,也是當時印度人認為是修行中最高、最究竟的境界,因此他們頗有興趣。在巴利文,滅受想定為abhi-sabba-nirodha。Abi意為「最高」;sabba是「想」;nirodha是「滅」。整句或譯為識(或想)的最高止滅(highest extinction),這是修行的極致。因此他們想知道更多有關滅盡定的境界。布吒婆羅繼續說道:
或有人作是說言:想之生與滅,係無因無緣。當「想」生起,則人有知覺(conscious);當「想」停止,則沒有知覺 。此為彼等所說之增上想滅。
布吒婆羅聽說滅盡定是指沒有知覺,這是非常嚴重的誤解,「滅盡定」不是指沒有知覺,而是「想」和「受」的止息。布吒婆羅又說:
而餘者作是說言:其實不然,「想」實人我也(是一個人的自我),它會生起和消失。當「想」生起,人便有
知覺;當想(perceptions)消失,人便沒有知覺。
布吒婆羅轉述他人的見解,並使用「增上想滅」(識最究竟的滅盡境界)這個概念,其實他誤解這個概念,佛陀稍後會向他解釋。
復有餘者作是說言:「不然,實有沙門婆羅門,具大神通與大威力,彼等於人,移想而來,掣想而去。移來則有想,掣去則無想。」此等人以如是說增上想滅。
復有餘者作是說言:「實則不然,蓋有天神,具大神力與大威力。其於人也,移想而來,掣想而去。移來則有想,掣去則無想。」此等人以如是說增上想滅。
印度自古以來便充滿迷信,以上的觀念便源於此。關於這個問題,佛陀認為:迷信和外力永遠無法使人了解實相(truth),無法使人覺悟。布吒婆樓接著說:
世尊,爾時,我心生念言:「世尊精於此法。世尊熟知增上想滅。」請問世尊:何者是增上想滅?」
讀這篇文章,好像把我們帶到古代的印度,使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經中的人物,彷彿我們也在現場一般,我們熟知他們的習慣和所關心的事。我們可以感受到布吒婆樓是如何的尊敬佛陀。佛陀回答道:
布吒婆樓,彼沙門、婆羅門認為;「想」的生起和消失是無因無緣的,這種見解是錯的。
佛陀對一些錯誤的見解,向來是直斥其非;而對於正確的見解,則一定會認同。佛陀接著說:
所以者何?有因有緣,人之想生;有因有緣,人之想滅。由於修習而一想生;由於修習而一想滅。云何修習?
佛陀此時尚未回答布吒婆樓的問題,因為「識的滅盡境界」是長期修行的結果,佛陀會從最初的修行說起。
布吒婆樓,今者,如來是應供、正等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者 、天人師、佛、世尊。
乃至身業語業,清淨具足,具足戒行,諸根之門,悉為守護。具足正念正知,自知滿足。
如來(Tathagata),Tatha意為「如」;gata指來或去;如來即是佛陀。上述的十個名號是形容佛陀的十個特質。
如來於此世間、天界、魔界、梵天界,於此大眾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自身證悟,為彼等說法。
天界指天人住的地方。天人和天使相似,根據佛陀的說法,天人在福報享盡後,會重回人間,所以他們必須修行才能再回到天上。在每一節禪修前,我總會默請天人和我們一起禪修,那些想禪修的天人自然會來。天界眾生的身體不像人類那麼粗糙,所感受到的苦也非常少,所以不像我們有修行的意願;而有些天人也樂於聞法,也會和我們一起禪修。
魔(Maras)即是撒旦,在這部經中,這個字是複數,應該譯為心魔(tempter)。我們心中都有天使和魔鬼。梵天
(Brahmas)是四禪天中最高的天界,他們不是創造者,不是造物主。
如來所說法,初善,中善,後亦善,文義具足,示教梵行,究竟清淨,無與倫比。
佛陀所教的法中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文義具足」。要了解經文並不難,我們必須去閱讀,並盡可能記住經中的內容。不只是學者,其他大眾亦然,試著去找出經中最有趣的部分。而對想修行的人而言,這是不夠的,只有當我們去實踐這些教法時,佛陀智慧的言語和精神才能進入我們的心中,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佛陀的意思,而他的教導才能成為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在這之前,我們只是知性上的認知罷了。
佛陀的教法(teaching)被稱為法(Dhamma);佛陀沒有教「佛教」,正如耶穌沒有教「基督教」。佛陀想改革婆羅門教,而耶穌則想改革猶太教,雖然他們都失敗了,卻各自開創了新的宗教,並改革已失去原有精神,並衰退到只剩下一些儀式和儀軌的宗教;今天,在每個地方都有同樣的問題。
佛陀接著說:
一個弟子因而出家,並受具足戒。
出家通常指成為比丘或比丘尼,並遵守出家人的戒律。出家人必須持戒,如果他們的心中沒有「法」的精神,可能會犯戒。對那些自願遵守戒律的在家人而言,由於他們看到持戒的益處,內心的掙扎會比較少。
佛陀尚未回答布吒婆樓有關較高層次意識的問題。佛陀主張先持戒,以作為修行的基礎。佛陀接著討論五戒-五戒是所有戒律的基礎。
今有比丘,捨殺離殺,不用刀杖,懷慚愧心,充滿慈悲,利益一切生類有情,而住哀愍 。
佛陀不只希望我們不殺生,還希望我們對一切眾生慈悲,並由衷的關心眾生的福祉。佛陀接著說第二條戒:
今有比丘,捨不與取,離不與取,取其所與,求其所與,毫無盜心,自住清淨(過清淨的生活)。
第一條戒可以對治嗔,第二條戒可以對治貪。在其他場合,佛陀建議以「布施」作為對治貪的方法,使我們放下「我」或「我的」等執著,並培養互相幫助、患難與共、慈悲等善念。
今有比丘,捨非梵行,淨修梵行,行出離行,捨離淫慾,自住清淨(過清淨的生活)。
第三條戒是不邪淫戒,在此改為「獨身」,即不淫。在比較嚴格的修行,不淫是最重要的戒律。出家人最重要的戒律即是不淫。如果破了此戒,比丘或比丘尼會被逐出僧團。有些在家人在三個月或六個月的禪修期間,也遵守不淫戒,這可以訓練一個人的獨立,也有助於克服強烈的感官慾望。
第四條戒佔了較長的篇幅:
今有比丘,捨妄語,離妄語,說實語,正直誠心,不欺世人。捨兩舌,離兩舌。不會把在此處聽到的話,到別處宣說,以免離間此眾。也不會在此處重述「在他處所聽到的話」,以免離間彼眾。因此當有紛爭時,他是個調解者;他鼓勵人們愛好和平,使人們和睦相處,快樂的過生活,所以他只說促進和平的話。他避免說惡毒的話(不惡口),只說悅耳的話(和雅音),以及令人愉快的話。
他避免無謂的閒談,只在最適當的時候說話,並說真實、重要、如法(Dhamma)和合乎戒律的話。他說的話被重視,因為都是合理的、合時宜的 。他說的話與最終的目標有關。
「欺騙世人的人」是偽君子,說一套,做另一套。大部份的人都有直覺能力,知道我們所聽到的究竟是來自說話者的親身經歷,抑或是道聽塗說。「因此當有紛爭時,他會是個調解者;他鼓勵人們愛好和平…。」此處的重點是語言可以帶來和平,我們可能讀了上千本的書,而不為所動;而由衷的、真誠的的語言,關心人類福祉的話語,則能觸動人心。
「他避免無謂的閒談,只在最適當的時候說話,並說真實、重要的話。」在其他經典,佛陀教我們說話前要先思考,用詞要精確,使人容易了解。「他說的話…與最終的目標有關。」這個目標是修行的最終目標-涅槃(Nibbana,梵文是Nirvana),Nibbana(涅槃)意
指「不再燃燒」,也就是所有慾望的止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我們可能不想放下所有的慾望。就世俗人而言,這種心態當然沒有問題,然而要知道,我們修行的目的是要證入涅槃-要止息所有的痛苦煩惱。
當佛陀說:我們應該說一些有益的、能激勵人心的話,談論「法」(Dhamma)時,應該正確的表達,並掌握重點。這種「法談」可以使我們解脫苦-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問題是我們如何達到這目標,我們必須找出「我不想放下我的慾望」和「我想去除所有的苦」之間的關聯。透過觀察苦如何生起的,我們可以在觀察時自問:「我甚麼時候開始受苦?」,「苦何時生起?」,「為甚麼我會受這種苦?」每個答案都會引起新的問題。假如你深信自己沒有苦,那麼可以自問:為甚麼我想要禪修。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察,因為它會使我們去思考是否我們真的沒有任何苦,並使我們去找出苦因,並永遠去除這些苦。
第五戒是不飲酒和不吸食麻醉物品,這部經沒有提到這條戒,取而代之的是對弟子們的告誡:「不可損壞種子和農作物。」在某些佛教國家,由於社會環境使然,這條戒被誤解為出家人不可以在園子裡工作;事實上,是指不要損壞農作物,而不是不可以照顧和種植花木。因為佛陀在經中教導苦行外道,這些外道是修行人,他們想知道有關修行的更高層次,而他們視「受持不飲酒和不吸食麻醉藥品戒」為理所當然,所以佛陀省去這條戒律。
佛陀接著說「不非時食」戒,這是沙彌和沙彌尼應該遵守的,而參加密集禪修的在家人也會受持這條戒。對我們來說,可能指不隨意打開冰箱,或是身上不帶巧克力,以免隨時想吃它幾口。這條戒律是希望我們在飲食上能節制;如果我們想要更嚴格的自我訓練,可以每天只吃一餐,或在某個時段禁食。
「他不觀看歌舞表演」,因為娛樂會使人分心,甚至會引起情慾,這些與貪慾或希望滿足感官之娛有關。如果我們想精進禪修,為了讓心保持平靜,最好能避免這些娛樂。
「他不著花鬘,不塗抹香水,不事裝飾」。世人無不想使自己的外表更迷人,這會使我們對自我產生執著。如果我們很富有,我們會用貴重的東西來裝飾自己,來突顯自我的價值感,認為:「如果我擁有貴重的東西,我就是個有價值的人。」這種想法雖然沒有明確表達,卻是一般人根深蒂固的觀念。
「他不接受金銀」指出家人不可做商業買賣,要過簡單、儉樸的生活,不追求世間利益。經文接著列出哪些是適當的供僧物件,也列出了哪些是不適當的,如:生米、生肉、女人、少女、男傭、女傭、羊、雞、豬、象、牛、馬、田等。因為這些東西會引誘僧眾去過世俗的生活,而忘記修行。
不為使者(替人跑腿),不為中介,不事商賈,不以秤升或尺,欺誑世人。不得賄賂譎詐…
有趣的是,起初佛陀度化弟子出家時並沒有制戒,他只簡單的說:「善來,比丘。」想出家的人便可追隨佛陀過出家的生活。後來出家的人越來越多,僧眾良莠不齊,有些僧眾禁不起誘惑,佛陀因此制定一些行為規範,讓僧眾遵守,並沿用至令。
欺騙和不老實是未證悟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或許有人不同意以上所說的戒律,然而只要遵守佛陀制定的戒律,就可以改掉一些壞習慣,而這些壞習氣是不利於修行的。稍後佛陀會回答布吒婆樓的問題。通常佛陀說法是先從日常生活的持戒開始,接著一步步的說到禪修,最後引導我們證入究竟實相。
第二章
守護根門:正念與正知
佛陀向布吒婆樓說明修行的起點-持戒後,接著說:
…布吒婆樓,比丘如是具足戒行,依戒而行,故無論身在何處,皆無怖畏。
要使事情完美必須經過訓練,智者不會把這種訓練視為強迫的,而會視為可以培養自制力,因為透過降服自己負面的本能(instincts)和衝動,我們會看破一切產生痛苦的假像。佛陀教的每一種法都在引領我們更接近這個目標。顯然的,「無論身在何處,皆無怖畏」會帶來安全感。如果我們沒有任何過錯,便不會失職或有罪惡感,因此會感到輕鬆自在。佛陀舉了一個譬喻:
猶如已灌頂的剎帝利王,已降伏所有敵人,故無論身在何處,皆無怖畏。比丘亦復如是,由於具足戒行,故無論身在何處,皆無怖畏。由於受持聖(Ariyan)戒,比丘有無咎之樂。
樂(bliss)指內在的喜悅,這不是禪修所產生的喜樂,而是知道自己無可責備,不再受慾望折磨之苦,因而產生的滿足感。Ariyan是聖潔的意思,受持聖戒比受持五戒需要更高程度的出離。例如,五戒中的第三戒是不邪淫,而出家人則要求禁欲(不淫)或獨身。
佛陀繼續討論下一步的修持-守護諸根。佛陀仍然不想回答布吒婆羅有關「識的滅盡」的問題,因為布吒婆羅仍無法了解正確的答案。
今有比丘,眼見可見物(外境)時,不執取總相(major signs),亦不執取別相(secondary signs)。如果他不守護眼根,貪愛、憂傷、不善心境將充滿其心。所以他守護眼根,使眼根受到節制。
佛陀接著敘述其他五根,經文如下:
今有比丘,以耳聽見聲音時…;以鼻聞香時…;以舌嚐味時…;以身體接觸外物時…;以意(mind)思考時…不執取總相,亦不執取別相。如果他不守護諸根,貪愛、憂悲、不善心境將充滿其心;因此他守護諸根,使六根受到節制。
佛陀接著說:
比丘由於受持聖戒,守護諸根,故有無咎之樂,比丘如是守護諸根。
這幾句開示經常被人誤解為不要看、不要聽、不要嚐、不要碰;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有了感官,就必須看、聽、嘗、碰、聞;禪修時,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的心不可能不去想。
當然不去看某樣東西便不會受它干擾,然而我們如何能不看東西呢?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們想持戒的話,正確理解這段話是非常重要的。「不執取總相,亦不執取別相」是甚麼意思?眼睛只看到顏色和形狀,其餘的都發生在心裡,以看到一塊巧克力為例:眼睛只看到一塊褐色的東西,是心在說:「啊!巧克力,一定很好吃,我想要一塊。」「不執取總相,亦不執取別相」是要制止這種念頭的生起。
這方法用在我們非常喜歡或非常討厭的事物上,特別有效。人最敏感的兩個感官是視覺和聽覺,我們可以選其中一個來修,觀察心有甚麼反應,並看看心如何編造故事(storytelling)。其實眼睛和耳朵並沒有選擇看甚麼和聽甚麼的自由,例如,耳朵聽到了貨車經過的聲音,心會立即反應:「貨車」,接著會反應:「真吵,吵死人了,怪不得我無法禪修。」後來發生的全是心的造作,和聲音沒有關係。聲音只是聲音,顏色只是顏色,而形狀只是形狀。
有時候,受持不淫戒的人會被告誡不要看異性,這怎麼可能?我曾遇到一些如此修行的比丘,最後造成不自然、尷尬的人際關係。你怎麼可能和一個故意不看你的人說話?這絕不是守護根門的意思,而是當眼睛看到形體時,心中標明(labeling)如「男」、「女」,便停在那裏,不要讓心再想下去,因為如果心再想下去,可能會生起貪或嗔,要視當時的情況而定。大多數人都能修持這個法門,一旦照著去做,生活會輕鬆多了。以上街購物為例,上街前,我們擬了一張購物單,都是真正需要的,然而當眼睛看到一堆堆包裝精美、大特價的商品,心馬上被吸引,最後我們買的要比實際需要的多。有些人逛街只是為了找一些吸引他們的東西;如果有錢的話,有些人把購物當成一種消遣,當成週末的節目。
如果我們很容易受外境影響,最好的方法是去觀察感官接觸外物的那一刻,並使「想」蘊不在心中生起-即不再標明事物。在此之前,要停止心的作用是很難的。例如,如果我們看到或想到某人,不論喜歡或怨恨他,或看到我們既不討厭也不喜歡的人,我們應該將心停在「標明」的那一刻,也就是知道對方是個人、是朋友、是男是女等,僅此而已,其餘的部份都是我們的慾望,這是守護根門的意思。
感官用來維持我們的生命,能看、能聽當然比失明、失聰容易生存,而大多數人認為感官的存在是為了帶來快感,我們就是這樣使用感官,一旦感官無法帶來快感,我們便會生氣,會遷怒他人。如果某人惹我們生氣,我們就會責怪那個人,其實跟那個人根本無關,那個人和我們一樣,也由地、水、火、風等四大組成,有相同的感官、四肢,也和我們一樣追求快樂,那個人根本沒有使我們生氣,是我們的心在生氣。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用在使我們快樂的人身上,他(她)和我們一樣也由四大組成,有同樣的感官,同樣的四肢,也同樣追求快樂,根本沒有理由去要求那個人使我們快樂,或在那個人不能為我們帶來快樂時責怪他,我們只需看清一點:他是一個人,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在這個世界上有芸芸眾生,為甚麼要讓這個人來決定我們的苦與樂呢?
我們能把根門守護好,便能防止慾望的生起,這樣我們便能更有捨心(equanimity)的過生活,而心也不會像蹺蹺板一般,起伏不定,當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心便往上揚;當得不到時,心便如蹺蹺板般往下落。在這個世間,無論在哪裏,無論在任何環境,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我們永遠滿足;世間提供給我們的只是感官接觸而已:看、聽、嘗、觸、聞和想,這些都是短暫的,必須一再的追求,而追求感官慾望會耗費許多精力和時間。事實上,不是感官接觸為我們帶來滿足感,而是心生起滿足感。
如果我們想要平靜、和諧的過生活,最重要的是要守護根門,這樣便不會因為想要所沒有的東西,或想推掉已有的東西而煩惱,這是兩個苦的因。只要我們能守護根門,不讓心超過標明的階段,那麼我們便能夠輕鬆自在的過日子。
心像極了魔術師,心能隨時變化,只要一越過想蘊(標明)的階段,心就開始變戲法,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貪和嗔很快就會生起。佛陀曾提到魔羅(Mara),即心魔(tempter)。魔羅經常和我們一起,並伺機入侵,其實誘惑是可以避免的,當誘惑出現時,我們必須去克服,我們可以在誘惑未生起前,便阻止它的生起,這是守護根門的意思。
佛陀在教導布吒婆樓有關「較高層次的識的滅盡」和禪修的方法前,仍有許多話要先告訴他。佛陀接著提到正念和正知。這種說法的次序也出現在其他經典:首先是持戒,其次是守護根門,接著是正念、正知,後兩者經常被放在一起。正念的巴利文是Sati,而正知則是Sampajabba(或譯為正智)。
比丘如何具足正念正知?今有比丘,若進若退,正知之;瞻前後視時,正知之;若屈伸手足,執持衣缽;若飲食嚼嘗,若大小便利,若行住坐臥,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於一切時,皆正知之,比丘如是具足正念正知。
正念有四個層面:即對身、受、心、法(想的內容)保持正念。身念住是其中最重要的部份,不只在禪修期間,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在禪修以外的時間不能保持正念,那麼在禪修期間也不能,所以必須時時保持正念,因此我們以「觀察我們的身體」作為第一個念處(身念處)。我們要覺知所有的動作;無論行住坐臥、穿衣、卸衣、屈伸手足,都要觀察。修習身念處最大的益處是能把心放在所緣境上,不會讓心到處亂跑。
修習身念處的第二個好處是能淨化內心。當我們在觀察
身體的每一個動作時,煩惱、忿怒或貪心就無法生起。佛陀一再的告訴我們要把身體當成正念觀察的對象。首先我們可以試著感受身體,可以碰碰身體。修身念處的另一個好處是,我們無須去找念處(觀察)的對象。如果我們能持續修習身念處,在短時間內,心就會平靜下來,心中不再波濤洶湧,因為當心在觀察身體的動作時,忿怒、貪慾、厭惡等惡心所就無法生起。
第三,正念可以讓我們的心安住在當下。最後,我們會發現根本沒有所謂的過去和未來。通常我們會把時間分成過去、現在和未來,事實上我們只能活在當下,只有當下才是真的,而過去和未來都是心所創造的,它們來自回憶和想像。許多人活在過去和未來,或活在過去與未來兩者當中,果真如此,那麼要保持正念和禪修會非常困難,因為正念和禪修只能在當下為之。
覺知我們的情緒和感受是第二個念處-受念處;第四個念處是法念處。我們將立刻討論第三個念處-心念處。在禪修時,法念處和受念處都是觀察的對象;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仍須修習這兩個念處。例如有強烈的情緒生起時,首先,我們要覺知它的生起,然後以善心來取代不善心,我們沒有必要受情緒影響。如果去追溯各種情緒是如何生起的,我們必能發現它來自感官接觸,這是顯而易見的。
同樣的方法也可以用來觀察我們的念頭,如果我們知道某些念頭是善的,我們只是觀察它,等它消失後,我們再以正念觀察身體的每個動作;如果是不善心,我們盡快以善心來取代。不善心停留在心中的時間越短,發展成負面心態的機會也越少。我們越能覺知我們的貪心和嗔心,便越不會讓貪與嗔在心中生起,也越容易從貪與嗔的煩惱中解脫。
第三個念處是心念處,心也是很重要的觀察對象。如果我們能在不善心發展成思考或情緒前便覺知到,那麼,取代的工作就會變得更容易。有些人的心念經常是負面的,並且很難改變這種情況,大部份的人都在正面和負面的心境中搖擺,也有人的心大部份時間是正面的。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的心境是負面的,心中的怨恨、妒忌和厭惡會引起負面的想法和情緒,那麼我們要避免這種惡心所的生起,並知道這些只是一時的心境而已,而我們所有的、所想的或所作所為,都是無關緊要的。一旦發現這些心境會使我們不快樂,就無需保留;我們越快樂,就愈能和身邊的人分享。如果自己都不快樂,如何能與他人分享快樂?我們不可能給人一些自己所沒有的東西,至於為甚麼有些人自稱可以,這是一個謎。
四念處是指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和法念處。正念意指純然的覺知,其中沒有些微的判斷。下判斷是正知(clear comprehension)的作用,以正知來判斷感受、情緒、心境和思想內容是善的還是不善的,以便有需要時可以取代。我們都有正知-有明辨的能力,有足夠的智慧去判斷。當然我們也有一切人類都有的小缺點,也就是那些不悅、憂慮、掉舉(restless)、煩亂的習氣,然而我們不要去執著這些缺點,有了正知,我們便能觀察這些缺點,並以善法來替代這些不善法。我們在禪修時觀察這些心念,並學著放下這些不好的心念,繼續觀察禪修的對象;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修行。
人為甚麼放不下消極的心態?唯一的理由是他們為自己辯護,給自己找理由去責怪他人或外在環境,這樣無法帶來快樂。在修行之旅中,我們必須如實的觀察自己,而不是希望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或希望別人怎樣看待自己。
坦然面對自己會帶來改變,在改變的過程中我們會有解脫的感覺,彷彿放下了重擔。只要保持正念,心會從散亂的思緒和反應中解脫。不斷對外在環境作出反應,會消耗許多心力,因為這些反應往往是吹毛求疵和帶有批判性的,有了正念便不會發生這些情況。
無論是按照字面意思或就比喻來說,正念指在所有的情況下,都能專注在自己的每一個動作上。當然,有時我們會失念,每當我們發現了,便再提起正念,這是我們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事。
正知有四個層面,《布吒婆樓經》沒有提到。第一是要覺知到我們想做或想說的是甚麼,並去觀察它的目的是否有益,如果是自我中心或只顧自己,這是無益的。一旦了知我們想說或想做的是有益的,就進入第二層面:要確定我們是否有適當的方法去達成,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第三個層面是:自問:該目的和方法是否如法,以另一個方式是去問是「佛陀是否同意?」我們根據所了解的佛法來自我檢查我們的目的和方法,最重要的是看看我們的言行是否合乎戒律,有沒有慈悲心?能否帶來幸福?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種行為能否使我們達到滅苦的目標?思考這些問題後,我們便不容易走向歧途。
世間有森羅萬象的事物,除非我們有凡事思考的習慣,否則很難避免造惡業,假如前三個層面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麼我們便可以付諸行動了。第四個層面(步驟)是:已經作了(說了)我們想做(想說)的事後,去觀察看我們是否真的達成目標,如果沒有,那麼要想想看有甚麼缺失。
以上是以「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最有益的方式」來解釋正知。首先,我們必須以正念來覺知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現象;接著,以正知來檢視我們的意圖,如此修習,我們的本能反應自然會慢下來,這是非常有益的,因為衝動容易犯錯,謹慎反而使我們走向正途。接下來,佛陀討論有關生活必需品的滿足。
比丘如何自知滿足?今有比丘,以袈裟護身,自知滿足;以缽食養身,自知滿足,並在獲得足夠供養後離去。如有翼鳥,任飛何處,只有羽翼隨身。比丘如是自知滿足。
在今日的工業社會中,大多數人所擁有的比所需要的多。佛陀說只有四資具-飲食、蔽身之所、衣服和醫藥是必要的。而大部份的人所擁有的東西遠遠超過這四種資具,雖然有些是必要的,而其他的是不必要的。去檢視一下我們是真的需要這麼多東西,還是出於貪慾,這是非常值得做的事。然後,再問問自己:「我對所擁有的東西是否滿足?我是否了解知足的可貴?我知道大部份的人都不了解
知足的可貴嗎?」我們可知道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是吃不飽、穿不暖,沒有醫藥,又沒有片瓦遮頂嗎?想想我們這些豐衣足食的人,是否認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呢?通常,我們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當我們看到的東西不是賞心悅目,或嚐到不合口味的食物,或碰到我們不習慣的事,我們往往會抱怨,而不會感激所擁有的一切。我們發現:去抱怨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比感恩擁有這些東西要容易多了。
佛陀曾經和弟子們在海邊漫步。佛陀對他們說:「諸比丘,若有一盲龜游於海中,而此海龜每一百年才浮出海面呼吸一次,而海中飄浮著一根木軛。諸比丘,你們認為這隻盲龜的頭能夠穿過這根木軛,浮到水面上嗎?」,「世尊,這是不可能的。」佛陀說:「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大可能。」佛陀接著說:「能轉世為人,而又諸根完備、四肢健全,又有聽聞佛法的機會,也是如此稀有難得。」
我們可記得這些教誨,以培養知足的心?在禪修時知足是非常重要的,心愈不知足,就愈難禪修,因為不知足會使心煩亂。由於我們認為自己的禪修並不是很順利,所以會不滿足;或是想到達某種境界,或是想證悟;任何一種不能滿足的想望(wanting)都會使內心混亂,使情況變得更糟。除非我們有知足的心,否則禪修會徒勞無功,我們的禪修會愈來愈差,而心也會愈來愈不知足。任何事情,只要我們認真去做,一定可以做好。如果我們總是不知足,不知足就會變成一種習慣,心裡會想:「我非常不滿,因為…」然後我們會為自己找許多理由,這些理由大都是很愚蠢的,與衣服、飲食、住所、醫藥無關。
我們應當記得佛陀說過「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們也應該知道,我們擁有所有維生的必需品,因此我們可以繼續修行,當我們充滿感恩,感謝良好的環境,感謝有那麼殊勝的機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禪修。不滿足的心會到處亂跑,想找到使自己滿足的事物。禪修會給我們帶來真正的滿足,首先,我們應該培養知足的態度,並感謝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四種必需品又稱為四資具(Four Requisites)。在現代社會,為了謀生和溝通所需,我們可能需要許多東西,而有些東西是無關緊要的,即使沒有這些東西,也一樣可以生存。有一種觀想(contemplate)很有幫助,也就是花點時間來觀想所擁有的一切,並心存感恩,而不去貪求其他事物。在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有不足之處,如果我們觀想這不足之處,那麼不滿足的心便會生起,並耿耿於懷。相反地,如果我們只想一些使我們心滿意足的事,那麼,滿足的心自然會生起。這個道理很簡單:每當我們將心放在某處,只覺知到該處所發生的現象。我們不要有一些負面的想法,然而偏偏經常如此,這是人們的毛病。我們習慣把心放在使自己不愉快的事上,即使知道這樣做會使我們受苦,我們仍然明知故犯。或許我們應該想一想:為什麼負面的想法會給我們帶來不愉快?愈了解自己內心的人,愈容易放下一些沒有幫助、又不能帶來平靜和滿足的事物。
知足者有非常輕鬆的感覺,因為放下了總是期待景況與人事變動的重擔。事物會如實呈現,如果不願接受這些事實,只會給自己帶來痛苦、煩惱;這就像在推一扇鎖住的門一樣,我們一再的推,直到推得手痛,仍然無法把門打開,如果我們夠聰明,就會接受這個事實,門鎖了就鎖了,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我們應該用這種態度來看待生命,一切事物本來如此,我們只能如實的接受。所有事情都以應該發生的方式發生,都各有自己的因和果,即使我們平日無法看清楚,不要緊,最重要的是,要把生命中所遇到的逆境當成一個個學習的機會。如果碰到不如意的事,把它當成學習的好機會,不要逃避,也不要期望它有所改變,因為這樣必定會使自己痛苦。我們要自問:「我從中學到了什麼?」無法從經驗中學習是極大的損失。
生活猶如一所成人教育學校。如果我們如此看待生命,我們會正確的觀察生命現象。如果我們希望生命充滿樂事,那麼我們必定會失望,除非我們了解到:我們來這個世界是要學習的(we are here to learn)。在這所成人教育學校,有各種不同的課程,我們被編入最適合某種課程的班級,這與年齡無關,而與我們內心的成長有關。每個人都要面對所需要學習的事,如果我們無法從中學習,無法通過考試,那麼我們會發現:我們又回到原來的班級,再學習同一門課程。直到我們的內心成長到足以通過考試,才能繼續修下一門課程。
布吒婆樓和我們一樣有許多課程要學習-持戒、守護諸根,以及培養正念正知,這些課程都有助於達到「識的最高滅盡」,而布吒婆羅在他的修行之旅中,必須了解和修習這些課程,才能達到最終的目標。
第三章
終止五蓋的作用
(比丘)具足聖戒聚,制御諸根,具足正念正知,自知滿足,離世閑居,或在靜處,或在樹下,或在山谷,或在巖窟,或在墳塚間,或在林藪,或在露野地,或在藁堆。比丘乞食而還,食後,結跏趺座,端身安坐,正念現前。
在這段經文中,佛陀開始討論禪修,我們知道不是把腿盤起來就是禪修,還要使「正念現前」。
在修習安般念(anapana-sati,數息觀)前,在觀察出入息能帶來任何重大改變前,我們必須先從佛陀所說的五蓋(hindrances)中解脫出來。
一、 貪欲蓋
(比丘)棄除貪欲,住於無貪欲心,離去貪慾,使心淨化。
這個蓋(hindrance)經常被稱為「貪求感官欲望的滿足」。如果我們被任何欲望所纏縛,很明顯的就無法禪修,
我們必須下定決心把慾望放下。經常困擾行者的貪欲有:「天氣太冷,太熱,膝蓋很痛,我的背部很不舒服,我好餓,我吃了太多東西,我想喝水,我覺得不舒服,我需要睡個覺。」在心中生起任何類似的念頭都會使禪修中止。
所有來自外在世界的事物必須透過感官進入我們的心,而禪修的體驗則無須依靠外境。一旦我們有入定的喜樂,便會發現由禪定所生的喜樂能對治貪欲。如果心能達到一境性(one-pointed),貪欲就無法生起。我們越能達到心一境性,心中便越少掙扎;不會為了食物、舒適、溫暖或其他我們想要或不想要的東西而掙扎。所有的苦都來自貪欲;貪欲越多,痛苦煩惱也越多,連「我想有一節很好的禪修」也是貪欲。
貪欲與錯誤的信念(belief)有關,也就是誤認為快樂來自感官接觸。我們當然有許多快樂的時刻,當我們不斷的向外追求感官接觸,認為它們會帶來滿足,就會封鎖我們通往禪定、清淨和離苦之路。只要我們沉溺在欲望中,就會受苦,這是沒有必要的,我們必須放下貪欲。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我們必須有正確的了解,加上堅定的意志才做得到。
一種捕捉猴子的陷阱最能說明這點。印度的獵人設計了一種用樹枝做的猴子陷阱,它是漏斗型的,開口很小而底座很大。獵人在底座放了甜點,猴子要拿這甜點,就要把爪子伸進很窄的漏斗通道,當猴子拿到了甜點後,無法把爪子抽出窄窄的通道,由於猴子通常不願意放下甜點,於是成了獵物,猴子只要張開手掌,便可以輕易逃出陷阱。我們也一樣,很難放下心中的慾望。
一旦知道苦如何生起,就不會受喜歡或不喜歡的念頭的影響,我們才會有好的修行,才能了解「放下慾望便能止息妄念」。一旦我們依此修行,馬上就會看到成效,然而要小心不要急於求成,因為急於求成的慾望本身就是苦,這是世俗的欲望。「我想要…,我非常想…」,所有類似的慾望都應該捨棄。解脫道上沒有甚麼值得貪求,只有需要完成的工作,我們要了解哪些是必須做的,目前手邊有甚麼工作要做,然後去做,僅此而已。
佛陀為五蓋作了比喻。貪欲如負債一般,我們欠了感官接觸的債,於是不停的還,又不斷的舉債。除非我們了解追求感官欲望的滿足就像不斷舉債,並成為我們唯一關心的事。一旦得不到所想要的,或是它不持久,我們就會不快樂,甚至會抱怨某事或某人。追求感官的滿足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我們沒有能力保留感官所接觸的東西,無論是景物、聲音、氣味、味道或念頭,都是生滅不已的,這種滿足要依靠外境產生,而在生滅過程中,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去改變它。
在譬喻裡,負債的人總想還債,意指我們經常要為追求愉快的感官接觸而憂心。一旦我們了解這種追求是沒有必要的,這就像還清債物一樣,我們不再欠感官的債,無債一身輕。正如佛陀所說的,這才是值得高興的事。知道我們不再追求感官欲望,這種覺悟會帶來很大的安全感和獨立感;相反的,如果我們放不下心中的貪欲,我們便會經常煩躁不安。
二、瞋恚
(比丘)棄除害心,棄除瞋恚,住不害心,普為利益慈愍一切生類有情,離去害心與瞋恚,使心淨化。
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打坐時,瞋心會有不良的影響。所以在每一次的禪修前,我們應該先對自己,然後再對一切眾生散發慈心。有些人發現很難去愛自己,因為喜歡自我批判和討厭自己。果真如此,這種人會很難去除貪欲,因為他們認為感官慾望滿足了,便能產生自我滿足感。他們有接受自我(self-acceptance)和憐憫自我(self-compassion)的心態,然而世上沒有可以永遠滿足的慾望,因此我們必須一再的追求,以滿足欲望,這樣只會帶來更多的苦。我們必須學習對自己散發慈心,儘管我們有許多缺點,一個愛自己的人,才能不挑剔、不批判的愛其他人。
對慈悲心而言,完美主義是沒有意義的,世上從來沒有完美的事物,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世事與世人應該是完美的」這種想法是多餘的,這種觀念會造成緊張和壓迫感,因為這種想法會產生欲望。放下這種不切實際的空想,以及放下欲望,我們會感到輕鬆和解脫。
假如我們很難對自己散發慈心,那麼可以修習兩種特別能生起慈心的方法。首先,觀想我們最愛的人,並對他散發慈心,然後再把慈心散發給自己,其中不可有任何欲念,否則這個方法會無效。散發慈心時,只有關懷、包容、想要幫助他和有禍福與共的感覺。第二個方法是回憶我們以前所作的善業。透過回憶,將過去的善業帶回當下,重新回味那些善行,覺得自己也是不錯的,此時,讓我們去愛那個以善心去做好事的自己。將慈心散發給自己後,我們應該想到地球上的芸芸眾生,他們也追求安寧和快樂,但只有少數的眾生可以如願以償,我們也把慈心散發給他們。
如果我們把對周遭的人或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人的敵意留在心中,我們就必須記得:越能放下瞋心和惡意,越容易禪修。佛陀說:當心中充滿瞋恨時,是不可能禪修的;而有慈悲心就可以禪修了,慈悲心是我們給自己的禮物。在禪修時,我們必須全心投入,毫無保留的投入禪修,沒有任何的「我」留下來,或是有另一個「我」想解決某個特別問題,想找一些方法來滿足某種欲望,雖然我已看到佛陀所說的法(truth)。
佛陀在一篇開示中,以替國王打仗的戰象作比喻。如果戰象只用腳來為國王打仗,那麼它不算忠心;如果只用頭打仗,而保護身體其他部位,也不算忠心;同樣的,如果只用象鼻,而保護其他部位,也不算忠心。只有在上陣時,這隻戰象用全身的每一個部位,全心全力為國王服務時,才是忠心的。我們在禪修時經常有類似的情況,我們會有所保留,我們會想:「我可以獲得甚麼好處?這是正確的教法嗎?怎樣才可以使禪修按照我的方式進行下去?當我的這個或那個欲望滿足後,我的苦一定會消失。」所有這些想法都會使我們有所保留,無法全心投入禪修。當心不散亂,達到住心一境時,此時,貪欲就無法生起,因為心完全專注(不會分心),不再有觀察者,只有經歷者〈experiencer〉,因為心已經和所緣境合而為一了。此時已進入完全的定。
佛陀將惡意和嗔恨比喻為身體的病苦。大家都知道生氣的感覺-熱、煩躁,非常難過,這些只是輕微的症狀。這是為什麼有人說:那些瞋心重的行者是最好的禪修者,因為總是感到不舒服,這使他們有很大的動力去修行。佛陀曾拿瞋心和膽疾比較-膽汁(壞脾氣)不斷在心中生起。
瞋心是三不善根之一,另外還有貪和痴。我們也有三種善根:慈愛、慷慨及智慧。我們可以全權選擇要加強哪些根。痴(delusion)意指錯誤的觀念,亦即認為有個實體稱為「我」,並且必須保護、支持、照顧這個「我」,而且要不斷滿足我的所有欲求。由於「痴」,當想要某些東西時,「貪」會生起;當得不到想要的東西時,「嗔」會生起。我們無法直接對治「痴」,因為貪和瞋太強了,障蔽了我們的智慧,一定要先對貪和瞋這兩個敵人下工夫,試著減弱他們的根。
禪修時,我們要去除瞋心。假如有特別不喜歡的人或事,在禪修前,我們可以告訴自己:「我將在下一節的禪修中,讓所有的不悅離去。」這一節禪修後,如果我們想繼續生氣的話,沒有人會阻止我們。如果我們的嗔怒連片刻都無法停止,就無法禪修。去除瞋心,就像從大病中康復一樣。
三、昏沉及睡眠
(比丘)棄除昏沉,棄除睡眠,繫想光明,正念正知,離去昏睡,使心淨化。
在禪修時,我們經常為昏沉及睡眠所困擾,這是第三蓋-昏沉及睡眠的例子,克服的方法是「繫想光明」(perceive light)。繫想光明有兩個方法,如果真的昏昏欲睡,在入睡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張開眼睛,望向光明處,直到我們醒覺,然後再閉上眼睛,在心中繫想光明。一般情況下,「繫想光明」能去除因缺乏動力和正精進所引起的昏沉及睡眠。正精進不是身心的緊繃和僵硬,而是覺醒與覺知(awareness)。
當禪修的心變得昏昏欲睡時,就無法覺知當下所發生的事情,就如踩在上了蠟的地板一樣,任意向四處滑動;心既無法覺知任何念頭,也無法觀察禪修的對象,這就是昏沉與睡眠,這時候我們應該暫時停止禪修。由於禪修使人心情頗為愉快,所以許多人會繼續禪修下去。
當心處在一種非醒非睡的狀態時,我們很難覺察到苦,我們要立刻捨離這種狀態,因為這是在浪費時間,應該睜開眼睛,並移動身體,讓血液流通,或拉拉耳垂,或揉揉臉頰;為了克服昏睡,最後可以站起來。我們也可以鼓勵自己:「現在是禪修的時候,希望我能禪修得最好(make the best of it)。」這不是希望能從中得到什麼,而是盡力而為。
如果「繫想光明」是自然而然的話,通常這是已進入禪定的徵兆。每當發現心不專注時,也可以刻意繫想光明,這時候的心或許已失去動力,或是從來都沒有修行的動力;或是忘了禪修的目的。如果能繫想光明,則能照亮心中黑暗的角落,這是五蓋的躲藏處。
佛陀將昏沉與睡眠比喻為坐牢,當昏昏欲睡時,我們便無法動彈,雖然我們有鎖匙,卻無法使用。我們必須有禪悅和精進,當有了禪悅和精進時,心會受到鼓舞;有一顆鼓舞的心,我們就可以禪修了。佛陀也說過:多了解一些法(Dhamma),對修行會有所裨益。
四、掉舉與惡作
(比丘)棄除掉舉,以及惡作,使心輕安,內心寂靜,去除掉舉,以及惡作,使心淨化。
我們要了解「內心寂靜」這句話的意思,我們希望禪修能使內心平靜,而佛陀卻說:內心要先平靜才可以禪修。當內心煩躁不安時,我們更要記住佛陀的話。我們要找出煩躁
的原因:「為甚麼我的心不平靜?是什麼欲望在擾亂我的心?為甚麼我會這麼不安?」如果心不能安止在一處,那麼身體也不能。掉舉(reatlessness)在我們無法獲得想要的東西時生起,所以應該觀察這個煩擾(agitation),仔細的找出這個欲望,並問自己:這個欲望滿足後,心是否真的會平靜下來?我們何不直接放下這個慾望,同時也放下了這個欲望所引起的苦和掉舉,使內心平靜。
在這段經文中,佛陀說到:「內心寂靜,使心淨化…」內心不但不再煩躁不安,由於欲望不再生起,心也得以淨化。這時心很輕鬆,有平靜的心(even-mindedness),感到自己和周遭打成一片,不再擔憂所缺乏的東西。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缺少甚麼,我們擁有一切所需的;只是我們的思想和觀念矇閉了我們,所以無法看到真相;如果我們能夠捨棄這些想法,禪修便容易多了。有一種想法是心需要靠外境才能平靜下來;事實上,平靜本在心中,只要放下對外境的執取,便可以使內心平靜,這取決於我們的心念。掉舉與惡作永遠和欲望有關,一旦覺察到這一點,便要立刻放下欲望,這樣內心才能淨化和平靜下來。
「擔憂」通常與未來有關,我們希望未來的事按照我們所計劃的方式發生,這種生活方式是荒謬的,因為太在意未來發生的事,會錯失當下,而當下才是我們所擁有的時刻,也是最重要的一刻。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掉舉」在心向外尋求滿足時生起。一旦了解我們已經具足一切所需,或許更容易放下心中的不安(unrest)。
許多人有做不完的事,有趣的是所有的事都是我們自己找的,即使事後有所抱怨,我們所做的都是自己選擇的。忙於各種活動使人覺得自己很重要,覺得自己也是個「人物」(somebody)。掉舉為日常生活帶來許多難題,因為掉舉會使人陷入不同的處境,而我們不得不去面對、處理,最後感到事情多到難以應付。我們應該知道掉舉是五蓋之一,是一種障礙。
佛陀把掉舉和惡作視為奴隸狀態,我們被情緒擺佈,讓它成為我們的主人,讓惡作、憂慮充滿內心,以致無法獨立思考。禪修者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不是指要去發明一套新的修行方法,以及獨自完成每一件事,沒有必要。我們非常幸運,因為佛陀的指導是垂手可得的。而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腦袋,能將佛法中不同而相關的部份連接起來,並且知道如何互相配合-起初看起來像一幅大拼圖,由許多圖片所組成,漸漸的我們知道它們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並能夠看到整幅圖畫之美。
五、疑
(比丘)棄除疑惑,心離疑惑,於善法無有疑惑,離去疑惑,使心淨化。
為了去除疑惑,我們要能分辨善惡,我們必須知道哪些事情有助於我們達到解脫的目標。而在這部經中所提到的目標是要培養一顆平靜的心,我們需要一顆平靜的心來禪修。疑會使我們錯過輕安(tranquility)的經驗,我們會懷疑自己有沒有能力禪修,以及擔心禪修太難,或許我們也會懷疑禪修指導,懷疑是否應該遵守禪修指導。事實上,長久以來的經驗証明,遵守禪修指導的禪修者都有很好的成果。這些指導來自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傳統,是非常可信和可靠的,這些禪修指導不斷的被實踐;而我們對修行的見解只是一些個人的看法,這種個人的見解往往受到自我形象和外在環境的限制,既不可靠也不可信。
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要接受佛陀的教導,並依教奉行,那麼,我們就不會心生疑惑。我們的心非常喜歡幻想(conjure up)各種的概念和可能性,有時或許能証明佛陀是錯的,這是非常好的消遣,尤其是當禪修不太順利時:「這套修行方法一定有不妥之處,我已經非常努力了,所以一定不是我的錯,或許佛陀並不是甚麼都知道的。」疑,彷彿是個狡詐的敵人,我們會懷疑佛、法、僧和導師,懷疑自己的能力,懷疑禪修指導,甚至整套教法。這些「疑」不但使我們難以禪修,甚至使我們無法修行,因為心忙著想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如果真的想禪修的話,一定要放下所有類似的想法。
我們也要放棄追求完美的理想,因為追求完美是一種執著;事實上,我們必須放下所有的觀念,只管修行。「疑」使我們很難全心投入去走修行之路,如果沒有修行的動機,修行道上會充滿荊棘。「疑」也使我們在各種教法(teaching)中游移不定,使我們無法投入任何修行中。我們一再嘗試新的方法,又半途而廢。全心投入指完全付出。要做到這點,我們一定要有信心。
佛陀說:「疑」猶如在沙漠中旅遊,身邊只有少量的食物,又沒有地圖,在漫長的旅途中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不確定甚麼是有利的和應該走哪條路,這種猶豫經常妨礙我們的修行。雖然我們知道:透過修行,我們的了解會更深入。禪修使我們的心變得能適應、有彈性、更柔軟,也因此能知道更多。
疑和審察(investigation)不要混淆不清。去找出自己與所接授的方法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對我有甚麼影響?我要如何修才能了解實相?」另外,「疑」不是信(belief)的相反,佛陀從不贊成盲目的信仰,而是希望我們對他所說的,能培養足夠的信心,使我們能夠在沒有疑惑下修行。
在另一部經典中,佛陀談到禪修的先決條件,首先是要知道自己的苦,知道苦從何而來,如何困擾我們。其次是從教法(teaching)中得到信心,知道自己也可以走這條修行的路。第三是為自己有機會能修行而感到喜樂。只有當這三個因素都具足時,禪修才會有成果。這裏所說的喜樂,並不是世人所謂的高興,例如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感激、高興;又如看到美麗的景色後,所感到的快樂等。而內在的喜悅(inner joy)是當我們找到究竟解脫的教法,以及我們正逐步邁向這個目標後產生,這非常有助於禪修。打坐時,如果我們在想:「唉!又要再坐一支香,我想我一定要撐到底。」這樣我們永遠無法好好禪修。禪修時,必須有一股很強的力量和振奮的心;雖然禪修能強化兩者,而我們從一開始就要有這種力量和心態。
每個人都有五蓋,而每個人都會發現某種蓋為我們帶來較多的麻煩,所以去找出哪個蓋是自己的敵人,是非常值得的。如果是「昏沉及睡眠」蓋,那麼就要繫想光明;如果是「瞋恚」蓋,就去修慈心禪;如果是「貪欲」蓋,就要去想慾望給我們帶來的苦,並放下這些慾望;如果是「掉舉和惡作」蓋,我們知道這和欲望得不到滿足有關,並試著放下欲望。我們知道掉舉和自我形象有關,也就是希望在世上佔一席位,被人欣賞,這些想法是沒有必要的。由於其他人都很努力的去建立自我形象,所以要有這種特別的見解是相當難的。
放下五蓋並非指把它們根除,使五蓋永遠消失。我們可以把五蓋視為花園中的雜草,如果我們不斷除草,就削弱了根的力量,使它們不再遮蔽好的植物;當我們有足夠的心力時,就可以根除五蓋。在這之前,我們的工作只是除草。
在每一節禪修前,我們自問:「現在我有沒有瞋恚的念頭?有疑惑嗎?有掉舉與惡作嗎?我感到昏沉和想睡嗎?我的心充滿欲望嗎?」如果有這五蓋,就要把他們放下,用慈心和平靜的心去對治,還要記得:修行是一無所穫(nothing to gain),以及放下一切(everything to get rid of)。
第四章:初禪
已經說明能專注禪修的先決條件後,現在要討論初禪(jhana)。有一點需要先說明一下:我們所讀的佛經是根據巴利經典(Pali Canon),而巴利經典是上座部佛教所根據的經典。所有讀過巴利經典的人都知道:禪那是解脫道的一部份。正如其他在這部經中解釋過的一樣-五蓋、守護根門、正念正知,都是解脫道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們真的希望修行會帶來喜悅和幸福的話,那麼我們必須遵循每一個步驟,不可以因為某些部份太難,或是有人告訴我們某些部份是不必要的,而付之闕如,因為這只是個人的見解和意見而已。
佛陀指出了整條解脫道,能遵守他的教導是最安全和有效的。本經不是唯一討論安止定的經典,還有許多經典討論安止定。我強調這一點的原因是,許多禪修者有安止定(meditative absorptions)的經驗,卻不知道他們所經歷的是甚麼。許多禪修者想尋找指導者,卻徒勞無功。讀了佛陀的開示後,我們可以依照佛陀所教的法來修,不過並不容易,大部份人都需要指導。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佛陀在經中的開示,佛陀說:「…(比丘)心知,已捨離五蓋…。」這點非常重要,在初禪,只是暫時捨離五蓋。五蓋在安止定中無法生起,在打坐時,我們絕對不可以讓五蓋生起。由於五蓋仍然潛伏在心中,所以我們不能讓五蓋生起。
我們要以慈心和悲心來禪修,心中沒有疑惑,沒有任何感官欲望,沒有昏沉與睡眠,沒有瞋心、掉舉與惡作。在禪修時,一定要降伏五蓋。事實上,我們自然會去克服五蓋,因為如果有任何一蓋生起,心會立刻變得激動(agitated),那時便無法禪修。相反的,如果我們有慈有悲,知足,並決心修定,不去想任何成果,那麼便能降伏五蓋。禪修會帶來輕鬆感,即使只是暫時捨離五蓋,我們也會感到很平靜。
捨離五蓋,觀察己身者,便生歡喜,歡喜者生喜,懷喜者身安穩,身安穩便覺樂,樂則心入三昧。
這裏的喜與樂仍然是世俗的層次,不是禪定的層次。巴
利語有不同的詞來形容這兩個層次,而英文就比較有限,歡喜(gladness)是一種放鬆和幸福的感覺,身體也會跟著安穩。有了安穩(tranquil)的身體,我們會感到喜悅;有了喜悅,我們的心會傾向專注,所有的禪修者永遠要記住這一點,內心的喜悅是禪修的必要條件;沒有喜悅便無法禪修。
這裏所說的喜悅來自安穩的身體,而這種安穩的感覺來自一顆樂於禪修的心。喜悅生起的原因有很多:知道自己有能力依法修行;能夠靜靜的打坐;或是身體健康。如果沒有這些喜悅,尤其是樂於修行,那麼當我們覺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時,便很容易忽視禪修。
沒有喜悅,便無法入定,雖然佛陀經常提到這一點,而我們卻很少聽到。佛陀說:身心要先感到舒適才能禪修;只有心感到喜悅時,才能入定。如果我們知道為了甚麼去修行,並且懂得欣賞自己的努力,單單了解這點便能帶來喜悅。
以上所說的是pamoda,即世俗的喜悅,還不是sukha,即禪定的喜悅。一旦能在沒有五蓋的情況下坐禪,整個身心都會感到平靜,彷彿身心合一一般,我們好像正在開展擁有巨大潛能的事業。佛陀繼續說:
(比丘)捨離諸欲,離不善法…。
「捨離」(detach)這個字經常被誤解,因為經中不會總是詳細說明是「捨離諸欲,離不善法」。而有些經文只提到「透過離欲,進入初禪」,這經常被理解為我們應捨離正常的生活,到森林裡住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森林中修行當然大有益處,卻不是必要的。「捨離」在這裡指捨離各種感官欲望或不善心所,也就是去除五蓋,捨離五蓋使我們有卸下重擔的感覺。
有尋有伺,離生喜樂,住於初禪。
巴利文vitakka-vicara 經常被譯為思考(thinking)及默想(pondering),這是不對的。所有禪修者都知道:如果心在思考和默想,根本不可能進入初禪。vitakka-vicara還有第二個意思,「尋」指將心導向禪修的對象 ;「伺」指將心持續放在禪修的對象上 ,這是這段經文的意思。
「…離生喜樂」,指已捨離諸欲,因而生起喜與樂。禪定中的喜與樂是同時生起的,「喜」在這裏指歡
喜,「樂」與喜同時生起,此時稱之為sukha(樂),我們稍後會了解這是二禪的重點。在初禪,「喜」以許多方式和強度生起,可能是大喜或是輕微的喜;也可能有許多感受,如輕安、漂浮、擴張、擴大、激動,這些都是喜的感受,而且永遠是喜悅的;這種狀態也被譯為趣味(interest),意指在這個階段,我們對禪修興致盎然。
此時,如果我們仍然在觀呼吸,我們將錯失良機。無論我們用的是哪一種禪修方法,都只是一把鑰匙而已,把它插入鑰匙孔,打開鎖,越過門檻,登堂入室-此處是我們所了解的內在生命。我們會發現心中所想的都是無關緊要的,都是與身外之物有關的事。我們的心充滿慾望、抗拒、本能反應、妄念、計劃、希望、理念和各種觀點。當我們的心變得專注,並感受到喜悅時,我們便能了解這個事實。
我們也知道這些感受一直伴著我們,我們沒有刻意使這些感受生起;能夠了解這點已經很不容易。這些感受一直都在心裏,只是心中的風暴使我們無法覺知到這些感受。一旦我們有觀察這些感受的能力,大部份的感官欲望和貪欲都會消失。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擁有我們所想要的,而這跟外在環境無關,也不會想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改變外境,因為這是無濟於事的。
初禪的體驗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巨大的轉變,然而,如果我們不繼續禪修,我們將無法獲得足夠的禪修經驗,內觀智慧也無法生起。
(比丘)捨離諸欲,而生喜樂,潤澤其身,周遍盈滿;全身到處,無不充滿,因離欲而生之喜樂。
如果我們只是身體某個部位感受到喜,那麼我們必須把喜擴大,讓整個身體都充滿喜悅。雖然這裏提到身體的感受,卻不是平日熟悉的那種感受。這種「喜」與極度愉快的感官接觸類似,卻不盡相同,它比感官接觸來得微妙,並更能使人滿足。我們可以控制它,只要掌握禪修的技巧,我們可以隨時讓這些感受生起,而且時間要多長,都可以自己決定。所有精通禪那的人都有這種能力,他們可以在四禪八定中,從任何一種禪那到另一種禪那,不一定要按照次序;也可以決定進入和離開的時間。當然這些都是在較高的禪修階段才能達到。
(比丘)入住初禪,因此先滅欲想,是時,生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perception)。
在這裡,我們知道情慾(lust)在初禪已經消失,當身體有「喜」的感受,情欲就不會生起,我們對所擁有的東西已經心滿意足,當然,欲望仍會伺機而起。如果從禪修中獲得的內觀智慧越來越深,我們進入禪那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強,欲望生起的機會也越少。
Lust通常指情慾,是所有感官欲望中最強的,也因此使許多人的生活非常混亂。強烈的慾望會使人喪失理智,所以找出對治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當內觀智慧生起時,我們會發現我們所渴求的一切早已在心中。經驗一再証明,我們有更多的機會放下情欲;即使不是完全放下,至少不會再干擾我們。
…是時,生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
「真實」意指我們真正感受到喜與樂。微妙(subtle)用來形容前四個禪那,它們是微細、微妙的禪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有類似的心境,只是比較粗糙。我們的喜與樂經常要依靠外境才會生起,我們無法使喜樂按照自己的意願生起。通常,一旦離開使我們快樂的外境,也會失去知足和滿足感。在禪那,不會發生這種事。由於禪那中的喜與樂是微妙的,而此時的滿足感也會持續不斷。
我們也知道我們可以隨時進入禪那;當進一步向二禪、三禪和四禪邁進時,我們會發現在日常生活中有過這種微妙的感覺,只是比較粗糙和不圓滿,它們是短暫的,無法隨心所欲的一再生起;而我們只要坐下來,入定,便可以一再擁有禪那的喜與樂。對心來說,以這種方式入定有很大的裨益,因為禪那可以消除妄念;所有的希望、計劃、擔憂、恐懼、喜愛、厭惡都會放下,這是放鬆的好方法,是我們可以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
「…(比丘)心知,有喜與樂…」也就是說,禪修者把注意力放在喜樂上。佛陀接著說:「如是由修習,故想(perceptions)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布吒婆樓曾問佛陀有關「增上想滅」(the extinction of higher consciousness)的問題。他想知道:識如何生起,以及如何達到無意識。布吒婆樓說:他聽說有四種方法可以達到無意識,但佛陀指出這些方法都是不正確的。佛陀說:「有因有緣,人之想生;有因有緣,人之想滅。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
佛陀接著教導布吒婆樓如何使心清淨,並因此得以進入初禪的方法。在這境界中,微妙的喜、樂想(perception)會生起;當心離開禪那,喜樂便消失,這是佛陀給布吒婆樓的回答。佛陀接著舉了一個譬喻來解釋初禪的感受,從這個譬喻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肥皂是怎樣製造的。
譬如善巧浴僕,或其弟子,於盥浴器,而撒澡豆,以水混合,澡豆受潤,因潤散碎,以一鐵片,塑造肥皂,由小成大,以油圍之,以至周遍,無不浸泡。比丘亦復如是,因離欲而生之喜樂,亦充滿浸潤全身;因離欲而生之喜樂,遍滿全身。
這個精彩的譬喻告訴我們:初禪的喜與樂應該是全身到處無不充滿。要切記:打坐時,不可以讓五蓋中的任何一蓋在心中生起,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必須觀察自己的心,要以正念去覺知自己心念,不要讓心去尋求滿足欲望的方法。
無論是自主或不自主(impulsive)的身體動作,我們都應該保持正念和持續觀察身體的動作,此時,心已經開始去除五蓋了。打坐時,如果五蓋已經不存在,那麼,沒有理由不能入定。一旦心想:「我要入定;我應該可以做到;或許我可以試試其他方法。」那麼我們以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我們應該單純的去「做」,心中沒有任何妄念,所有的妄念都是人想出來的,是心想出來的,所以不能反映真相。實相(truth)則完全不同,透過各種禪定的境界,我們會更接近實相。當然,除了禪定外,我們還有其他的工作要做,至少我們可以透過修定來提升自己的心。
每次禪那結束時,以及在每一節好的禪修後,我們應該做三件事:首先要知道出定時,所有喜樂的心境都會消失,禪修者應該觀察整個消失的過程,並知道喜樂也是無常的,不要千篇一律的說「無常」就算了;有些人聽過和說過「無常」無數次,以至忘了這個詞的意思,只是人云亦云的說:「一切都是無常的。」觀察可意的境界如何消失,重要的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教義(teaching)的精神,這必須親自去體驗。我們可以讀上千本的書,可以背上千首的偈頌,這些都是紙上談兵,沒有益處,智慧只在親身體驗中生起,別無他法。
我們每時每刻都有體驗,如果我們對所體驗的事物有正確的了解,我們早就開悟了。例如,我們在每一次的呼吸中體會到無常,可是許多人對未來仍懷有無數的妄念。我們不了解只有當下這一刻才是真實的,未來和過去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當下是可以把握的。人沒有固定不變的實體,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假相。
我們都知道念頭是無常的,會自然生起和消失。事實上,我們寧可念頭不要生起,因為我們希望能入定,可是我們又相信:「是我在想,這些是我的念頭。」我們應該觀察這種想法。通常,當我們擁有某樣東西,我們會有管轄權,然而,所有我們現在和過去「所擁有的」念頭不是已經消失了嗎?擁有這些念頭的「我」哪裡去了?是否消失了?還是不斷「擁有」新的念頭?哪個「我」才是真的?是過去的我,還是現在的我?每當新的念頭消失時,那個「我」又到哪裡去了?前後的念頭之間會有間隔,那時的「我」又在何處?是度假去了嗎?我們如何把它帶回來?當然是透過不停的想。
這個被誤解的經驗是產生「我」的假象的因。退出禪那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要知道禪那是無常的,同時也要知道念頭、情緒、呼吸、以及身體都是無常的。
禪修後第二件要做的事是,扼要重述剛才的經驗:怎樣入定?用甚麼方法?方法本身並沒有絕對的好壞,對你有用的便是好方法。人們執著某種特定的禪法是很普遍的現象,因為對他們而言,這種方法很有效,行得通,因此認為其他人也應該採用。這是不對的,由於每個人的根器不同,適合某人的方法,不一定適合他人。例如,有些人發現慈心禪很容易使他們入定。如果慈心禪修持得法,一股強烈的感受會生起,通常從胸口,這是很舒服、很溫暖的身體感受。有時,除了溫暖外,還會感到喜與樂。一旦有任何感覺生起,我們應該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感覺上;較強烈的感覺是與身體有關的,也是我們應該觀察的地方。
只要能夠入定,用甚麼方法都一樣。那時,我們才可以說:「我在禪修。」在此之前只能說:我在修習某種法門。雖然我們很少去分別兩者的不同,但是佛陀早已告訴我們。
有些人透過修習掃瞄觀察(sweeping exercise) 來修定,如果修持得法,入定時,有一股非常喜樂的感受會生起,此時,應該停止觀察,把注意力放在喜樂的感受上,然後,如佛陀所說的,再把這種感受擴大到全身。
另一個方法是修習遍處(kasinas),即顏色遍。如果我們很容易就觀想出某種顏色,那麼,我們可以觀想一個圓的色盤,把它放大,並完全融入,這也可以使我們進入初禪,這是修習遍處禪(kasina meditation)的目的。
或是修習數息觀,當呼吸變得微細,光便會出現,也可以把光擴大到全身。如果我們能使這種光持續一段時間,這光不但會圍繞我們,而且一股非常愉悅的感覺會生起。
有許多方法可以入定,當然我們不需要在一次禪坐中使用所有的方法。如果發現慈心禪很適合,就用來修定;假如我們自然而然就會觀想顏色,而在觀呼吸時,顏色障礙了修習數息觀,那麼我們應該改為修習遍處禪。同樣的,如果觀察身體很容易專注,便應該用這種方法,所以用哪種方法修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坐禪時,我們很高興知道我們有極大的潛力去證悟。
所有有耐心和堅持不懈的禪修者都能進入禪那,心自然會入定。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禪修者都渴望能入定,他們或許不知道禪那這個詞的意思,或安止定是什麼,卻渴望能從永無休止的念頭中解脫出來。雖然有時這種渇望是不自覺的,卻有可能。當一個沒有成見的人初次聽到禪那時,通常的反應是:「啊!我知道某些東西是存在的(there was something)。」
有時,初次體驗禪那時,我們記得原來小時候曾有這種經驗。小孩子通常會自然而然的體驗禪那,這比想像中更普遍。在成長的過程中,上學、家庭、性愛都會干擾我們,於是這些事便被遺忘。成長後,在我們飽受眾苦後,去禪修並達到初禪,記憶又會重現。
當佛陀仍然是菩薩悉達多.喬達摩(Gotama,或譯為瞿曇)時,他離開皇宮和家人到森林禪修,他從某位老師處學習前七種禪那,並且一進入初禪,就記起他在十二歲時,曾進入初禪。故事與佛陀的父親有關:佛陀的父親淨飯王是個小國的統治者。在春天來臨時,他們有春耕節,根據傳統,國王應該先翻土,淨飯王帶著十二歲的太子去參加春耕節,太子要和國王一起扶著犁,一人扶一邊。然而當典禮時間到了,卻找不到太子,淨飯王派一位大臣去找,發現太子在一棵樹下打坐,而且非常專注,渾然忘我;為了不打擾太子入定,大臣回去告訴淨飯王,淨飯王說:他會自已翻土。
稍後,在十二到二十九歲期間,太子沉迷在各種欲樂中,他結婚了,並育有一子。最後,他決心要去解決人類受苦的困境,於是他去森林禪修。由於他在前世和小時候都有進入禪那的經驗,所以很容易就能入定。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像太子般容易入定,然而,年幼時曾有禪那經驗的禪修者,的確比較容易入定,而我們就必須更加努力,去上一些訓練耐心和意志力的課。
佛陀從不曾說:初禪不會引起執著。這種觀念是佛陀涅槃數百年後,註釋家所提出的。禪那的體驗不但不會引起執著,而且能使禪修者有充沛的活力和迫切的想去禪修,因為我們會發現禪那的心和世俗的心大不相同。即使迫切感沒有生起,也會有「這不可能是全部」的想法,而會有想一窺究竟的想法。所有的智者都應該知道:禪修的目的不只是獲得樂受而已。雖然感到快樂,然而我們知道禪修不只於此,所以會頗有興趣的繼續禪修。
此時,禪那的心是純淨和明潔的,這點非常重要,純淨的心是禪那最可貴的收穫之一。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了解純淨。首先,心中沒有任何五蓋和煩惱;其次,它可以帶來清明。當某種東西是純淨的,它也是清明的。如果窗子是髒的,那麼我們很難看到窗外的景色;而擦乾淨後,我們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我們需要清明的心來禪修,以獲得內觀智慧。
純淨的心來自勤奮和持續的修行,來自「自我了解」和知道自己該做些甚麼。清明的心是真正要追求的,因為清明的心使我們能了解我們的經驗。一旦有了清明的心,我們會儘可能不再污染自己的心;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擁有的清明的心如珍寶一般,所以會保持警覺,以免遺失。這顆純淨和清明的心,可以粉碎一切迷惑、假象,讓我們看到世間的究竟實相(absolute truth)。
為了證得佛陀所教導的深湛的內觀智慧,我們需要一顆清明的心。清明的心來自絕對的專注,此時沒有任何妄念;只要有妄念,表示心還在世俗的層次,此時,我們只能看到心中的妄念。
第三步是:在每一節的禪修後,我們應該觀察禪修的體驗,看看是否有新的觀智生起。這種觀智特別有啟發性,因為是從親身體驗中生起的。佛陀是個非常實際的導師,他教導前四個禪那時只用數字表示,而不替它們命名,以免後人故做解人,依文解意,我們只需依教奉行即可;而從第五禪到第八禪都有名稱,我們稍後會討論。
禪修時,自然可以達到這種心識境界。我們可以從基督教和其他神祕主義教派的作品中讀到有關禪那的記載。他們所用的術語或許和我們的不同,而經驗卻是一樣的。《七寶樓台》(Interior Castle)是指導修女們的書,在書中,作者聖德雷莎(St. Teresa of Avila)提到七種禪那,她以夢幻的(visionary)方式敘述,而今恐怕很少人能解讀。由於她的敘述非常詳盡,讓人覺得這些經驗只是她個人的體驗;相反的,佛陀的教導就非常實際,不可能讓人誤解,因為佛陀的開示是針對每個人。其他基督教的神祕主義學家,例如Meister Eckhart和Francisco de Osuna也修習禪定,當然他們對禪那的描述也各不相同。
我們處在科技主導的時代,而不是宗教主導的時代,禪那的方法漸漸失傳了,但也不一定就此消失。藉著佛陀所留下的「法」,我們很幸運可以接觸到這些禪修方法。
有些人能夠在沒有人指導下入定,這是心專注一境的結果,也有人在大喜或極度緊張中進入禪定,而且並不罕見;而其他人進入禪定只是透過專注,專注於所緣境。
禪修是一門心的科學(the science of the mind),既然是科學,就可以解說和重複驗証,而且必須包括所有的心境。我們熟悉一些世俗的心,如思考、判斷、快樂、不悅、渴求、排斥等。世俗的心經常處於二元狀態,在二元狀態中,「我們」和「外界」是對立的。如果禪修無法帶來不同的體驗,那麼也無法使人滿足。
透過禪那,我們所體驗到的高層次的心識狀
態,顯示我們只是在這個世界,卻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知道,雖然有這個身體和心,我們仍然可以超越;這是為何佛陀教導每個人,透過禪那來證得內觀智慧的原因。在所有敘述解脫道的經文中,無不是從持戒開始,一直說到開悟為止,中間的禪那(jhanas)從來沒有遺漏過。有一點要提醒大家:我們打坐不是想要獲得喜樂的感受;相反的,我們只是遵循我們所選的方法去禪修-對我們而言是最好的方法,並持之以恆,這樣就夠了。
第五章
第二禪和第三禪
在這部經中,佛陀對布吒婆樓說明整條解脫道:首先是持戒,其次是守護諸根、正念正知、知足,去除五蓋,以上都做到了,禪修者才能進入初禪,這就像地圖一樣,一步一步引領我們到達目的地。所有人都知道如何使用地圖,如果我們不按照地圖上的標誌走,就會迷路,假設有人要從洛杉磯開車到紐約,只看紐約的地圖是沒有用的,我們需要一份從出發點到目的地的地圖才有用,而且還要以英里來標示到達目的地的里程。
討論過初禪後,佛陀繼續教導二禪。在以下的經文中,尋、伺被譯為思考和默想(pondering)。
復有比丘,滅除尋伺,內心寂靜安詳,住心一境,此時無尋無伺,沉浸在由禪定所生之喜樂,入第二禪。
剛開始,我們的心專注在呼吸上,然後繼續觀察出入息;二禪不需要這兩種工夫(即尋與伺)。由於進入初禪時,心已有足夠的定力,能保持穩定。之前,心仍然很不穩定,必須透過禪修才能穩定下來。在開始階段,心會跑掉,不能專注在禪修的目標上,所以要不斷的把心專注和固定在禪修的所緣境上。在這個過程中,喜樂的感受會消失;事實上,是我們的定力消失,心的感受依然存在,只是沒有任何感受而已。
我們可以專注在喜樂上,而不是專注在呼吸或慈心禪或其他禪修的目標上,我們可以把心只放在感受上。當知道身
體某一部位有最強的感受時,便直接觀察這個部位的感受。我們不是在觀察身體,而是觀察身體的樂受,因為樂受在身上,所以我們要找到那個部位。如果不能掌握這個方法,我們必須從尋、伺開始,行不行得通,要看禪修者的定力。
當訓練有素時,我們可以專注在樂受,並由此進入二禪。我們要在樂受中停留一段時間,完全投入,並覺知樂受的生起,大約十到十五分鐘就夠了,此時,心必須安止不動;而不再專注於樂受,必須刻意去做。在另一部經中,佛陀指出,由於知道身體的樂受仍然是粗糙的,禪修者仍需追求更高的層次:心的感受(emotions)。
一旦放下身體的樂受,我們會專注在內心的喜悅上。這股喜悅已在心中,我們只是改變專注的對象而已。此時,喜仍然存在,這時感到身體很輕,身體的感受消失了,彷彿沒有重量。如果有足夠的定力,身體不會不舒服,也不會疼痛。當然,退出禪那後,這些苦受可能會生起。此時,喜已經非常明顯;因為「樂」能對治掉舉和惡作,所以樂(sukha)能使心平靜。如果我們沒有樂受,有時試著輕輕的說「樂」這個字,可以幫助我們獲得禪悅。當我們的心專注在這個字時,便會進入禪定,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有效,有些人發現這樣會妨礙入定。
喜與樂都有興奮(excitement)的成份,我們會覺得喜樂好像在頭部的某處,當然這只是印象而已。當我們剛進入初禪時,會有強烈的興奮感,會想說出心中的感受。當我們培養禪修的習慣後,最初的興奮感會消失,而會有很微細的興奮感。我們還未達到真正的平靜,因此必須一步一步的朝著目標前進,前一步是下一步的因,每一步都是因與果。透過禪定會生起喜悅的感受;由喜(delight)生起樂(joy);當我們體會到如此殊勝的喜悅,怎麼可能沒有樂受?大部份的人從未體驗過這種內在的樂,因為他們必須依靠感官接觸才會快樂。所以如果能找到內在的喜樂,我們就能獲得許多觀智。
…是時,先滅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起由定所生之喜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自知心有喜樂。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經中的想(perception)其實是意識(consciousness)的意思,所以這部經也叫《心識的各種境界》(States of Consciousness)。在此處,佛陀說:透過修習,可以生起某些意識;透過修習,可以滅除某些意識(即:「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我們知道:心有時快樂,
有時痛苦,經常想得到我們所沒有的東西,或想捨棄我們已經有的,因此沒有完全平靜和喜悅的感受,或許我們不知道這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
我們平日為了謀生,以及和人打交道時的心識狀態永遠是二元的;一邊是「我」想要某些東西,另一邊是和「我」相對的外在世界,或是和「我」相對的你。「我」永遠與外在的人事對立,這樣,心不可能平靜下來。
我們都熟悉這些心境,大部份的人認為只此而已,由於這種信念,他們就向外追求滿足和快樂。開始禪修後,我們會發現:我們會有全然不同的心識狀態。這個理解對人有極大的衝擊;之後,我們會深信不疑。修行越久,對這些心識狀態越了解,大悲心就會生起。這種高超的心境與日常的心識狀態比起來,實在高尚多了,因此我們會充滿悲心,想去幫助他人,讓別人也能解脫痛苦。
佛陀在三十五歲開悟,在八十歲時去世,他一生都在幫助別人,使人們從痛苦中解脫。經典上記載著,佛陀每天都在教導,即使天氣險惡,身體有恙也不例外,不論到哪裏,無論路途有多遠,佛陀都是走路去的,由於當時的交通工具是用牛或馬拉的,佛陀不忍心把自己的體重讓動物去承受,所以佛陀從不乘車。現在仍有一條戒律禁止出家人乘坐由動物拉的交通工具。經上也記載佛陀每天早上都會禪修,並「張開悲心的網」,意指佛陀用天眼去觀察有誰願意聽聞法。佛陀說:「眼中只有微塵」的人不多,由於知道他們會接受「法」(Dhamma),所以前往渡化。
初禪有「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也就是說,進入初禪有「從捨離感官欲望、五蓋和其他不善心而生的喜樂」;在二禪則有「從禪定中所生的喜樂」(定生喜樂),也就是說,進入二禪,定力會加深。在初禪,偶而會有微細的妄念生起,也會聽到聲音,只是沒有平日清楚,這表示聲音對心的影響非常小。在二禪,聲音的影響更小,我們好像坐在玻璃圓罩內,所有外面的聲音都被隔開了,干擾也減少許多。隨著禪那的進步,定力會越來越強,漸漸的會住心一境。
這樣的專注能使心清淨,而心清淨會帶來清明,前者引生後者。有時,佛陀的教法被稱為因果的教法,因為他的指導非常清楚,明確,引導我們一步一步的邁向解脫道;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因,我們很容易了解,而「了解佛陀所說的法」是修行的起點。雖然了解佛陀所說的法,無法立刻帶來平靜和觀智(insight),但不了解「法」,就不可能進步;了解「法」,才有動力去修行,此外還要有一顆開闊的心,假如心不開闊,所有佛法的知識都沒有用處。我們說法可以說得舌燦蓮花,可以寫出博學多聞的作品,但永遠無法從痛苦中解脫。如果不打開心扉,便無法了解「法」。了解「法」,便能生起信心,使我們樂於修行。
退出禪那或在任何好的禪修後,我們要知道坐禪後的三件事,首先是觀察所有經驗都是無常的;其次是記得通往禪定的道路;第三是:我們要自問:「從這個經驗中我學到了甚麼?以及觀智有沒有生起」。
進入初禪,禪修者有喜樂的感受,心立刻體驗到一種高超的、廣闊的心識狀態;這種心識狀態迥異於「想要這個,不要那個」的消費者心態。廣大的心識使人了解到:生命中有許多境界遠超過感官所能體驗到的。即使是最愉快、最微妙的感官接觸,例如鮮花、彩虹、落日、詩等,雖然這些景物沒有任何不善,因為都是外在的,要依賴外境快樂才會生起,然而,外境無法永遠給我們帶來快樂。我們認為落日餘輝令人陶醉,事實上,是心沉醉在落日而生起愉悅,所以是心使自己陶醉,而非外境。我們經常認為快樂來自外境,然而外境只是引起感官接觸,使我們的心完全專注,以致渾然忘我,在那一刻失去了「我」的感覺,此時,沒有「人」在想:「我要這個;我想要有這個東西。」一旦外境(如落日)消失了,喜樂也會消失,而「我」又恢復原狀。隨著所生起的念頭:「我」要去追尋那醉人的落日,因為落日能帶來樂趣。這個例子說明事實是:我們經歷了許多事情,我們需要證悟,只是我們不完全了解這些經驗而已。我們需要「法」(Dhamma)來指導我們,然後才能如實的觀察事物。
我們知道有各種層次的心識,也知道所有的喜悅都來自內心,不假外求,是內心的清淨和專注使我們體驗到這種喜悅。由此可知,我們所追求的,心中本自具足。大部份的人向外追求滿足、幸福和快樂,他們不知道感官接觸的快樂必須依靠外境,所以是不可靠的。
在二禪,當我們體會到喜,我們知道:這種喜比以前所體驗到的更微細,而且毋須依靠外境。此時,整個人沈浸在喜悅中,這是感官接觸所沒有的。禪修者知道:進入二禪可證得第二種觀智,此後毋須再追求愉快的感官接觸-雖然這種愉快的感官接觸仍會發生,而我們的生活也會有極大的改變。追求感官欲望會耗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無論能否得到所想要的東西,都不免受苦,例如只得到一部份,或有人從中作梗。
禪那會大大的改變人的生活習慣,因為我們會把禪修的經驗融入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感官依然如常運作,用眼睛看,用耳朵聽,我們會品嚐、觸、嗅、想,然而我們不會無止盡的追求感官之娛。
長期的禪修會使感官更敏銳,禪修者在長期禪修後,發現大自然比以前更綠,天空也變得更藍,當然,天空和葉子並沒有改變,而是受覺變得比較敏銳。此時,禪修者不會追求感官之娛,也不執著或想擁有這些樂受,禪修者自有禪悅,沒有絲毫欲望,所以才會有一顆清明的心。通常,我們從未注意到感官之娛所帶來的苦,這是執著所產生的苦,想要擁有所引起的苦。在禪修時,我們只有單純的感官接觸,不會執著外在的事物,這是因為我們知道:不需要向外追求內心已有的東西。
此時,內心的平靜仍未達到不可動搖的境界,卻足夠為日常生活帶來寧靜、輕安的感覺。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或去任何地方,當然,我們仍會做某些事,事實上,我們會做得比以前更好,因為我們不再執著結果如何,更明確的說,是不執著「快樂來自成果(result)」這個觀念。我們去做,是因為事情需要有人做,我們會輕鬆的做,完全不會緊張。我們知道:有比世俗之樂更美妙、更微妙、更大的快樂。我們不是鄙視或棄絕世間,而是對世間不再有任何期望。既然沒有期望,當然就沒有失望。此時,與任何人都能融洽相處。
佛陀在《沙門果經》(Samabbaphala)中提到二禪:
(比丘)由定所生之喜樂,潤澤其身,周遍充滿;全身到處,無不遍滿定生喜樂。
我們千萬不要懷疑喜樂如何生起。喜樂都是心所(mental concomitants),卻在身體出現,例如,我們體驗到的樂是在胸口處,這是修行的心。喜樂是一種心理狀態,是一種感受,而我們卻指出它在身體的某個部位,我們必須透過這身心相關的地方才能有所體驗,別無他法。在二禪,「喜」在幕後(background),而「樂」則在幕前(foreground),並從頭到腳趾,充滿全身。修慈心禪時,樂也是從頭到腳趾,遍滿全身。假如我們能夠在修慈心禪時做到這點,便更容易進入二禪。如同初禪一般,佛陀也為二禪舉了譬喻:
譬如有水,從深泉湧出,其水不從東來,不從西來,不從北來,不從南來,而時有驟雨。由此深泉湧出涼水,以此涼水,潤漬深泉,周遍盈滿,此泉之水,無不遍滿。比丘亦復如是,定生喜樂,潤澤其身,周遍充滿;全身到處,無不遍滿由定所生之喜樂。
這段經文很有用,因為通常只在胸口處感受到樂,然而我們可以擴大這樂受,使喜樂充滿全身,只有此時,對二禪才有完整的體驗。當我們全身充滿喜樂時,這時我們才知道:世間的樂無法與二禪之樂相比。因為二禪的喜樂是大喜,讓人有滿足感,也因此,我們的心境改變了。
我們發現:我們不依靠外境也可以如此快樂,這種內心的喜悅使我們充滿信心,並有一種解脫感,也使人變得誠實、和自我依靠(self-reliance)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下一步:三禪。
由於內心充滿禪悅,這種喜樂可以對治五蓋中的掉舉與惡作,因此非常滿足。這種滿足感和前面所說的不同,為了能好好禪修,我們必須對所處的環境感到滿足,感謝生命中所擁有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們感到輕鬆和滿足。我們必須刻意去想生命的某些特質,並去觀察這些特質,此處的滿足感是相當不同的特質,這種滿足感來自禪悅,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我們一直想要的-充滿喜悅。
無論禪悅是多麼讓人喜悅,多麼讓人滿足,在一段時間後,我們仍要放下這種大喜,我們會有心往下沉的感覺,這只是一種感覺,不是真的往下沉。初禪和二禪好像在頭部發生,而三禪則有更深的感受。佛陀是這樣形容三禪的:
復有比丘,離喜住「捨」,正念正知,以身受樂(身體有快樂的感受),如諸聖所說:「捨念樂住」,入第三禪。
在這段經文中,「捨」(equanimity)出現了,事實上「捨」是四禪的特徵,所以有時很難去分辨三禪和四禪。修行的步驟是這樣的:首先放下禪悅-喜與樂,是刻意的放下,而不是由於心不專注而讓禪悅消失,果真如此,禪修會中止。這樣修持比較好:先進入二禪,體會禪悅後,再放下心中的喜樂。在另一篇開示中,佛陀提到:禪修者在二禪所體驗到的樂仍比較粗,所以要進入更微細、更微妙和更高的境界。
有些人很難放下二禪的喜樂,而有些人則未曾體驗過,修行道上有各種障礙,只要持之以恆,就能究竟解脫。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訓練自己的心,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耐心和毅力,有沒有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心態,我們一定要放下那種追求成果的情結(achievement syndrome)。為甚麼呢?因為內心本自具足,毋須向外追求。
如果我們不專注,內心的喜悅便會消失。我們知道:這
是另一個說明真相的例子,我們只能覺知心所專注的對象,此時,內心會感到輕鬆和滿足;首先,平靜和輕安會生起。「捨」(equanimity)指滿足,滿足就是「捨」。正念正知(clearly aware)是形容心一境性,這時,心完全覺知和警醒。「身體有快樂的感受」是所有禪那的特徵,而且非常快樂。不同的是:初禪是身體的樂受,二禪是微妙的禪悅-內心的喜樂,而三禪的樂則來自知足和平靜。
內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意味著智慧已經生起,內觀和智慧兩者同時生起,而且是透過親身體驗才會生起。經中以吃芒果來譬喻。如果我們不曾吃過芒果,有人給我們非常詳細正確的描述,甚至附上圖片來說明「這就是芒果,以及它的味道如何」。我們可以欣賞芒果的圖片和說明,卻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除非親自品嘗。佛陀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教導我們。由於得之太易,我們很容易忘失佛陀的教導。
由於內心的知足與平靜,另一種觀智可能生起,在禪修時,我們不要去想所發生的事,因為這涉及念頭的生滅過程。一旦有了體驗,觀智會自然生起;我們知道:只要心無所求,心就會知足和平靜,內觀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重大的影響。我們的心有各種欲望,有些慾望相當微細,而有些則相當荒謬。然而,我們知道:我們有各種慾望,這些欲望只會給我們帶來煩惱和傷害;而在三禪所生起的滿足和平靜,比欲望的滿足要殊勝得多。了解這點後,我們就可以把欲望放下;放下了慾望,同時也捨棄了因想望(wanting)、掉舉、想要獲得和達到目的所產生的「苦」。
無願(wishlessness)是一道通往開悟的門。怎樣才能找到這道門?透過體驗才能珍惜它的價值,至少要有短暫的體驗。當然,三禪無法使人開悟,但卻能帶來平靜和知足,這讓我們體會到無願的滋味。
「無願」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來面對生活,我們可能已經淨化某些欲望,然而我們知道:即使是最微細的慾望,也會使我們掉舉(restless)。對「無願」的體會,使我們「離苦的能力」大大增加,我們終於嚐到芒果,無需問人或查書,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無願,也知道「知足」指無願無求。
在禪那,我們比較容易體會由喜樂所生起的無願,而在日常生活中就難多了。然而,透過不斷的修習,直到「無願」成為一種生活態度,我們就會一直有「無願」的體驗,而心會更習慣這種心態。
如果不加以應用,觀智(insight)就會退失,正如學了一門外語卻不練習一樣,之後,當我們再度聽到,就會記得我們曾學過這種語言,再勤奮努力,就可以回想起來。觀智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不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很快就會忘失。直到有人提起,我們才知道自己也曾有這種觀智,這時,才會加以運用。重要的是,我們要把內觀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要經常練習,不斷進步,那麼,觀智便成為我們的了(不會再忘失)。
佛教經常使用兩種語言,一種是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另一種是法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the Dhamma),是我們談論究竟實相時所使用的語言。佛陀同時使用這兩種語言,他談論世俗的、日常發生的事,也解說究竟實相。我們必須知道兩者的不同,知道何時使用哪種語言。當佛陀談到禪那時,雖然他談的是高層次的心識狀態,而他所用的仍是世俗的語言,因為仍然有「我」在體驗禪那。除非我們能改變心識狀態,否則我們會發現很難了解這個層次的術語。
此時,先滅「定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生捨(equanimity)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捨樂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perceptions)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在這部經中,這段經文的最後一句一再出現,這是針對布吒婆樓和他最初的問題:「想或意識如何生起?如何滅去?」佛陀告訴他在各種禪那中意識的生滅過程。這段經文中的「捨」是一種滿足感;而「樂」是潛在的,只有前兩個禪那有樂受。當我們感到滿足時,是不可能不快樂的。
佛陀以譬喻來說明三禪:
譬如青、紅、白蓮,一一蓮池,諸蓮皆生水中,皆長水中,皆浸水中,為水所養,此等諸蓮,以水潤漬,由頂至根,無不遍滿其中。比丘亦復如是,其身無喜,以樂潤澤,周遍充滿;全身到處,無不遍滿無喜之樂。
佛陀所說的兩個譬喻都提到「遍滿」。在二禪,必須從頭至腳,全身充滿喜樂;而三禪則是充滿「無喜之樂」或捨心。由於大部份的人不知道捨心的意思,所以用滿足或平靜來形容更貼切,而我們對滿足和平靜都有相同的認知。而三禪的平靜,比我們在世間所體驗到的任何事都來得偉大。
有趣的是,我們的內心都有這種平靜,只是我們心中有許多「戰爭」,除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外,還有我們內心的衝突,以及家庭和工作環境的爭執等。而平靜本來就在心中,只需專注(concentrate)就能發現。令人驚訝的是,只有少數人能夠了解,即使在禪修時,很少人能夠在禪修時發現心中的平靜。只要我們能使內心平靜,就能改變整個生命,甚至改變他人,因為人與人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即使是在山洞中禪修的行者也能透過意念影響世界,何況大部分的人都不住在山洞裡,所以一定會互相影響。如果我們把內心的平靜散發出來,其他人會感受到,也可能因而受益,甚至被吸引而想要效法他們。
此外,還有一種普遍意識 (a universal consciousness),所有人都是普遍意識的一部份。所有的心識都在普遍意識中,假如我們,無論一個、二個、十個,或是一百個人擁有平靜的心,又能夠保持一段時間,並改變自己的生命,那麼這平靜的心就會進入普遍意識中,而且經常如此。同樣的,我們的心念進入普遍意識後,又會回到我們的心中,像是回音一樣。如果我們沒有可觸及(can be touched)的內在體驗,普遍意識就無法把平靜送給我們。
佛法不是與世人無關,不是「只要我有平靜的心就夠了,即使這世界毀了也與我無關。」佛陀從來沒有這種念頭。佛陀從開悟那天開始,一直向人宣說解脫之道,結果佛法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並傳到這裏。
在這部經中,佛陀談到心的統一(unity of mind)或心一境性,另外的意思是意識的統一 (unity of consciousness),這是在禪那中生起的非常微細的意識,這種意識使我們了解:人與人之間並非彼此分離的,我們都是互相關連的,都活在同一個世間。當我們對禪那的體驗越深,這種覺知便成為一種經驗。這種意識的統一能增長慈心和悲心,因為此時沒有「我」與他人之間的隔闔,只有一顆平靜的心,別無其他。
一旦心能夠提升,並超越平常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通常是負面的,而且與分析、邏輯推理和知識有關。我們可以提升所有的心識,並去改變環境,而不是讓環境來改變我們。以下的觀念是嚴重的錯誤,也是一般人常有的觀念,也就是認為我和環境是對立的,我要操縱環境,以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因為我與外境根本沒有界限,我與他人、與整個自然環境都沒有界限。我們與他人與外在環境是互相依存的。如果我們想要有較少污染的環境,首先要有一顆較少污染的心,而這顆心有能力達到更高的心識境界。
以上所談的心識境界,雖然不限於禪那中的境界,卻奠基於禪那才會產生。
第六章:第四禪
雖然在禪修時,我們不一定能入定,然而知道禪修的心所能達到的境界,以及禪修的心如何改變生命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在解脫道上我們只走了幾小步,我們仍需了解整條解脫道,然後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目前的位置,繼續解脫的旅程。
復有比丘,捨樂離苦,已滅憂喜,入第四禪,不苦不樂,捨念清淨。
這段經文有時會被誤解,認為前幾個禪那有苦有憂傷(grief),而真正的意思是:到了這個階段,已經沒有樂受和苦受,取而代之的是捨心和正念。如果要描述此時的禪那,以「心一境性」來代替「正念」會更貼切。事實上,「捨」是四禪的成果,心體驗到寂靜,當然此時不會有「這是捨心」的念頭,因為一旦有這種念頭,我們的心便不再平靜。
我以一口井來比較三禪和四禪的不同,三禪就如我們坐在井邊,把頭伸進比井邊安靜得多的井內;要體驗四禪,就要到井底。在不同階段的禪那,我們會體驗到不同程度的平靜,這是很明顯的。禪那也可以比喻成把身體完全浸在海裡,而井的譬喻更能突顯出禪那境界不斷的深化。在三禪,平靜已經很明顯,禪修者仍會聽到聲音,除非聲音非常大,否則不受干擾。當心越來越專注,聲音會消失,因為心完全專注在寂止上,所以不受任何干擾。
在禪修以外的時段,我們不可能有這些體驗,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平靜和滿足的時候,但總會受到外界干擾,我們不斷的看、聽、嚐、觸、嗅和想。雖然我們認為:我們只是單純的聽或看,事實上,心會吸收和消化我們所看到和所聽到的,此時,心無法完全寂止。如果我們想要完全的寂止,完全的平靜,觀察者必須與被觀察的對象暫時融合,合而為一,除了這個方法外,別無他法進入四禪。
前三個禪那,在某種程度上,觀察者和所緣境是對立的;在四禪,這種對立不存在,因為觀察者非常微細,讓人感受不到有「人」的存在,唯一可形容這種狀態的詞,是心已經沈入「寂止」中。事實上,觀察者並未真正消失,只有在證果時才會消失,稍後我們會談到這點。說觀察者與所緣境合而為一,意指在禪那期間,捨棄了我執-自我堅持(self- assertion),所以許多人怕進入深定,因為他們的自我在從中作梗。無論放下自我是多麼的短暫、多麼不徹底,對許多未曾禪修的人來說,是讓人駭怕的,所以寧願退出也不願讓心沉入寂止。這是常見的現象,不要緊,因為我們可以一再的嘗試。這就像對自己的游泳技術沒有把握,不敢到深水的地方去游一樣。一旦我們有完全寂止的體驗,我們會了解:只有暫時捨棄我執和「自我存在」的欲望,以及對任何境況的欲求,才能進入寂止狀態,我們才會了解:捨棄自我是多麼的美妙,以後會更想徹底捨棄我執。
四禪可以使心力大大增加,大多數人都過度勞心,白天不停的思考,晚上不停的作夢。心是非常珍貴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和心相比,而我們偏偏不讓心有片刻的休息。只有當「心」停止思考、沒有反應,不再有情緒反應,不再觀察外境時,心才能回復本來的清淨。在前三個禪那,心只能瞥見這種境界;而在四禪,心能不受干擾的體驗寂止的境界。經常修習四禪,能使內心更清淨,心會更清明,也會更有力量。
強而有力的心是很難得的,大多數人的心都有習性,一聽到甚麼或讀到甚麼,心馬上會有習慣的反應。如果接受某種特定的思考方式,心就會遵循這種方式。要能夠獨具慧眼、獨立思考,並看透外在的事物是很難的;而四禪能強化心力,所以能看透外在事物的虛幻不實。
如果我們過度勞累,不睡覺,沒有充分的休息,會發生甚麼事?數日後,我們會非常衰弱,無法正常生活。而一談到心,我們認為:即使從未讓心休息,心仍能以最佳狀態運作。佛陀稱未經訓練的心為「醒著睡覺」,這指心無法覺知到我們所碰到的事物,例如我們都會遇到無常和苦,如果我們想從中尋找體驗者(experiencer),我們將一無所獲,因為我們並不了解這些真理,雖然我們有所體驗,卻無法識別(recognition)。
當我們退出四禪後,我們會有恢復精神的感覺,這是心的力量。一方面,我們讓心休息來恢復精力;另一方面,暫時去除我執後,心會完全寂止,此時,心中沒有任何念頭,在四禪,心終於能夠放假,回到本來的清靜。通常我們放假後會比平日更累,不是嗎?而四禪的假期就非常寧靜。我們會放下一切引起我執的事物,這意味著我們了解「有自我」是錯誤的觀念。此時我們已略嘗解脫的滋味,而向道之心也會大大增強。
在四禪,我們更容易證得捨心。「捨」是七覺支 的其中一支,是最高尚的情感。我們會經歷不同層次的捨心,首先是當不如意的事發生時,不再激動。這可能是因
為我們認為:這不是應該有的反應,或是我們不想看起來很愚蠢,也可能是自我壓抑,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想通了。長遠來說,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受影響,反正,一切事物都會消失、壞滅,此時,我們要讓捨心生起。
佛陀曾談過五神通(ariya iddhis)。Ariya是神聖的意思,而iddhis是神通。神通經常被形容為魔法般的神奇力量,例如可以瞬間將身體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有人問佛陀:是否有必要具有這些神通?佛陀說:「我會告訴你五種神通。」只是佛陀把「神通」的意思改變了,並給予完全不同的解釋。佛陀所說的五種神通是:第一,每當遇到令人不快的事,我們要立即從中找到快樂的一面,不要讓自己變得消極;以正面的心態來看待事物,此時,捨心便會生起。
第二種神通是,每當碰到快樂的事,能立刻看到它不快樂的一面,這樣,我們才不會陷溺在欲望裡,捨心才會生起。所有令人快樂的事物都有一個共同點-無常,我們必須記住這點。大部的人認為他們相當了解無常,也能接受生命中的無常,事實上,他們把無常給忘了,而且經常如此。我們應該記住:我們所接觸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生命中的每一刻,無論是快樂或痛苦,只是永恆中的一剎那而已。為了去除貪欲,以及去除對令人快樂的事物的渴望,我們必須知道快樂有無常的一面。
第三種神通是,我們要從非常不喜歡的人事物中看到他們的可取之處。例如,假如有一個很不討人喜歡的人,我們知道他和其他人一樣也有苦,因此也值得悲愍;他也同樣追求幸福,也需要人幫忙。如果遇到逆境,我們以積極的觀點來看,認為這也是學習的機會,如此才會心情開朗,才不會生氣和變得消極。在修習一段時間後,捨心就會生起。
另外兩個神通相當類似,指能同時看出可意和不可意(unpleasant)事物的正面和反面特質。第五種神通只有阿羅漢-即開悟的人才擁有,阿羅漢能毫不費力的同時看出事情的正反兩面,而不會生起貪或瞋。佛陀時代,沒有記載下來的經典,佛陀所說的法,都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下來,而有些內容是重複的,這樣比較容易記得。
以捨心、平靜的心來面對自己的貪與瞋,這就是清淨之道,這是第二種捨心。第三種捨心是不會退失的,因為我們對無常有深入的了解,如在指掌之間,而我執也被減輕到不會障礙捨心的生起。會發生的事總會發生,一切事物都是緣生緣滅,如此而已。如果所發生的事合我們的意,那很好;如果不合我們的意,那也無妨。這種捨心由內觀生起,在四禪,捨心變得非常穩定。
每一種觀智都以平靜的心為基礎;沒有平靜的心,便沒有觀智,所以在四禪所體驗到的完全的寂止是觀智必要的基礎。從四禪所生起的觀智,使我們了解:只有放下我執,這種捨心或完全的寂止才會生起。一旦我們有了這種體驗,就可以隨心所欲的讓捨心生起,而毋須像以前那麼費力的讓捨心生起。
值得一提的是,捨心的遠敵是興奮、掉舉和焦慮;而近敵是冷漠。冷漠經常被用來保護自己不受傷害,特別是那些曾經有不愉快的經驗,曾經受到傷害,或是無法控制情緒的人,他們常常會自我保護,不要有負面的情緒。為了避免沮喪、憤怒和嗔恨,他們壓抑所有的情感,結果就變得冷漠。築起冷漠這道牆後,他們不再感受到慈心和悲心;也不會把感情放進去,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他們:放入感情,只會產生不愉快的結果,這種態度使他們把心扉關上。有時候,在觀察全身時,會發現自己有冷漠的問題。如果以正念觀察全身時,無法覺察胸口的感覺,這是一種障礙,感覺上像是碰到一道磚牆或水泥牆或非常堅硬的東西,我們好像穿上了盔甲,用來保護自己,在感情上不受傷害。
冷漠之所以被稱為捨心的近敵,是因為兩者非常相似,也很難分辨它們的異同。我們可能會認為已經超越了所有的興奮、激動和煩擾,這時才發現我們並未培養人性中良善的一面。捨心是透過內觀生起,而冷漠則是一種自我保護,兩者截然不同。由內觀所生起的捨心,不會妨礙慈心和悲心的生起。捨心和冷漠也有相同之處,如果不求回報及沒有任何期望,捨心和冷漠會很容易生起。所以我們花一點時間去觀察自己是否有冷漠的問題,這是很值得去做的。
是時先滅捨、樂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不苦不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不苦不樂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不苦不樂指沒有情感,所以沒有樂受和苦受。為了達到完全的寂止,即使是三禪的滿足感和平靜也要捨去。此時,我們的心已經被捨心和正念淨化,因而能超越苦與樂。在我們體驗到完全的寂止前,必須有一顆清淨的心;在四禪,必須具足正念和心一境性,心如如不動。而在前三個禪那,心可能會輕微的動搖,而在四禪,心不會有絲毫的動搖。為了放下前三個禪那的樂受,我們必須有捨心;此時,樂受、喜悅、滿足和平靜全部都要捨去。
「具有不苦不樂之微妙真實想」是微妙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內心沒有樂受或苦受,因為此時內心是寂止的。退出四禪後,我們會自問:「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我們才知道有不苦不樂的感受,有平衡的捨心。我們通常不會這樣說,而會說:「只有寂止,沒有觀察者。」也知道它的意思。
佛陀為四禪舉了譬喻:
譬如有人,由頂至踵,以白淨衣,被覆而坐,全身到處,惟白淨衣,周遍全身。比丘亦復如是,純淨清明,充滿其身;惟純淨清明,遍滿全身。
千萬不要誤解「身」這個字,這是四禪的境界,雖說是「身」,卻不是指身體的感受,而是全身的感覺。因為身體無法感受到捨心和正念,以及清明和清淨,心才能感受到。所以我們覺得整個人沉入寂止的狀態。如果以存在(being)來代替「身體」,經文的意思就會更清楚。
如是心寂靜純淨,無有煩惱,離隨煩惱,柔然將動,而恆安住於不動相中,爾時比丘,以心傾注於智見。
這些心的特質都是禪那的結果。在四禪,我們不會有這些體驗,因為心是完全寂止和平靜,不可能有任何念頭。出定後,我們可以觀察入定前後的心境,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心境是如何改變的。
在其他的開示中,佛陀說:在退出三禪或其他禪那後,會「以心傾注於智見 」;在四禪、五禪、六禪和七禪,出定後特別有用。「智見」指能如實觀察一切事物,這是如實知見,透過親身體驗來了解實相。「知」指了知所看到的事物,「見」(vision)並非指看見一幅畫的看見,而是把所體悟到的法內化,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在進入禪那後,尤其是進入三禪後,心能夠觀察不同的實相,這是沒有進入三禪的人所無法窺知的。這裡的實相是指「無我」(no personal identity),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找到一個有實體的自我。有人會質疑說:「如果沒有自我,那麼是誰在禪修?」或者問:「感到心煩意亂的是誰?」問這種問題的人,不承認人們是生活在錯誤的觀念中,也不認為這種錯誤的觀念會帶來無盡的煩惱。這種人認為:「既然我在這裡,一定有『我』在。」這種認知屬於世俗諦的層次,無法帶來解脫和自在。
在這個層次,我們可以幫助自己,如果我們能淨化我們的心念和情感,就能減少煩惱,而且我們一定要這樣做。至於究竟解脫、完全自在,只有在了解佛法的最終目標後才能逐步接近。
從以上的引文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我們想要有如實的「知、見」,必須有平靜的心。如果心到處攀緣,是不可能看到實相,也不會了解一切只是身心的生滅現象,別無其他。我們在讀過許多有關佛法的書後,在理智上接受「無我」的教義,然而要在內心深入體會「無我」,如果有一顆喜歡感官接觸的心,喜歡到處攀緣的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反而會有「自我」是真實的這個假相。
透過禪修,我們會發現隱藏著的清淨的心。清淨的心沒有任何執取,也不會想要「捨去」(getting away from)。這是清淨的、透明的心,是普遍意識的一部份,這種心沒有個體,沒有任何慾望。如果我們的感官沉迷於外境,我們的心忙於反應外境,無論我們是否喜歡這些外境,我們的心仍須知道是何種外境。到了這個階段,有了一顆平靜的心,我們會有不同的內在體驗。
如何去了解「無我」?佛陀接著說:
彼知是事:我身由色成,四大種成,父母所生,粥飯所養,為無常、破壞、粉碎、斷絕、壞滅之法。又我之意識依於此身,與此關聯。
我們的身體是由四大(地、水、火、風)所組成的。地大的特質是堅硬,作用是支持;火大即溫度,作用是毀滅和生成;水大指液體,作用是凝聚;風大的特質是推動、支持,作用是移動。我們很容易看到身體是由四大組成,別無其他。「父母所生,粥飯所養」說的是因和果。身體也有生成的因,我們自己就是身體存在的因,我們以食物來滋養身體。出生時便有了身體,渇望繼續生存是再度投生的因,沒有貪欲便不會出生,人不會無緣無故出生的。宇宙萬物根據自然法則在運作,一切井然有序,不會亂無章法。
當我們觀察身體時,知道身體不是「我」。這怎麼可能?身體就是我,只要照鏡子就可以知道:「這是我啊!」有許多方法可以觀察身體只是身體而已。首先,身體是無常的,身體不斷在改變,會逐漸老化,這是身體無常的特性,大部份的人都能泰然接受這真相,只是認為身體不夠美好而己。再以呼吸為例,如果我們憋氣,想使呼吸變成「常」,會發生甚麼事?大概會窒息,甚至死去,呼吸不可能是常的(permanent)。當我們修到正念現前,能深入觀察身體的本質,所體驗到的不只是身體的移動,而是發現身體不斷的變化,因為細胞會不斷壞死和重新分裂。科學家發現:人體細胞每七年會全部更換一次。還有更多的事實,例如,我們把食物吃了以後,會變成甚麼?我們必須消化、吸收和排泄,進去又出來,身體內沒有恆久不變的東西。我們一星期前吃的東西都會消失,我們必須一再的吸收養分。
人一旦相信「這是我的身體,身體就是我」,就永遠無法減輕欲望,因為大部分的欲望和身體有關,花些時間來探究這點是值得的。我們認為可以使身體變得完美,有人說:身體不會罹患癌症,因為身體本身便是一個大的癌細胞。看看身體的排泄物,沒有一樣是吸引人的,為了保持健康所以必須排泄,沒有人願意把這些排泄物放回體內。如實的觀察身體,身體是人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許多苦由身體產生,由於要不斷滿足身體的欲望,在許多方面,我們被身體所「困」。
我們知道身體由四大元素組成,也會觀察身體中的四大元素。例如,我們可以感受到身體的堅固和堅實(compactness),也可以站在樹旁觸摸堅硬的樹幹。當我們站在草地上,能感受到草上的露水和草的汁液;我們也可以在唾液、眼淚、汗水和血液中觀察水大;我們可以在體溫和地面的溫暖中觀察火大;我們可以從自己的呼吸和臉上的微風來觀察風大。我們可以觀察風如何吹動雲朵和樹葉,從而知道身體是如何移動的。我們知道所有物質都是四大所成,我們的身體和其他物質並無不同,同樣由四大元素所組成,所以佛陀說:四大是所有生命的基礎。
知道身體的不完美是很重要的,這並非指要去排斥、否定身體,或認為:「如果我沒有身體該有多好」,而是知道身體所帶來的麻煩。透過了解無常,我們知道自己遲早會死,這不是理論上的了解,或希望死神暫時不會降臨,這不是將來的事,而是時時刻刻會發生的事,我們隨時都會去世;我們所有的念頭、情感、呼吸和全身都不斷的在變化。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不斷的在生起和消失。了解這個真相,我們也同時了解:每天早上起床就等於再生一樣,所以根本毋須去思考死後會發生的事,因為生滅現象每一刻都在發生。隨著身體老化,這種再生變得越來越脆弱,直到完全停止,所以說死亡就在當下。
我們當中有人記得昨天下午四點三十分在想甚麼嗎?不可能的,一點跡象也沒有。我們連昨天的事都不記得,更遑論上一生的事。我們會記得生命中重要的或令人興奮的事或情境,而這些是非常稀有的,其他的都成為歷史,漸漸被遺忘。
身體是「無常、破壞、粉碎、斷絕、壞滅之法」,我們很容易生病或遇上意外。要毀滅一副軀體一點也不難,隨時都可能,尤其在戰爭、在致命的爭執和意外中。
當我們思考佛陀所說的話,我們需要觀察身體是否真的屬於我們,還是由渴愛所生,四大所成,必須以食物來滋養,是無常的和容易被毀壞的?一旦發現這些都是因與果,發現身體並沒有實體,就能了解:其實我們對身體的主宰力非常有限。沒有人願意生病、背痛、感冒或頭痛,然而誰也免不了。如果我們真的擁有自己的身體,怎麼會讓這些事發生?
另一個誤解是:如果我們的心很清淨,身體就不會給我們帶來麻煩,這是目前流行的「新時代」思潮中的一項謬論。連佛陀都會生病去世,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會死,在座的每個人都會死。如果真的有人可以長生不老,為甚麼從來沒有人做到?從來沒有事實,也沒有任何宗教能使身體不毀壞。我們當然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正如照顧自己的房子一樣。無論我們將房子整理得多好,也不會把房子視為自己,或認為房子不用修理和永遠不會毀壞,沒有人有這種想法。這個身體好像我們的房子一般,我們應該盡力使它保持整齊清潔,僅此而已。我們永遠無法使身體完美。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去觀察這個身體,並自問:「是誰擁有這副軀體?它有甚麼功能?為何身體會做那麼多我不要它去做的事?」
「又我之意識依於此身,與此關聯。」這是內觀的第一步,也就是了解人由身和心所組成,心又稱為識。現在流行的新時代思潮又有另一個觀念,認為身心在本質上是一體的。這種觀念不但不可能,事實上,還會給人帶來痛苦。因為如果身心真的是一體的,人就無法以捨心來面對身體的疼痛。這個觀念的用意是好的,可是與事實相悖,沒有用處。然而,的確有共相意識(unity consciousness),以共相意識來觀察世間,我們會發現:我們與一切眾生共存在宇宙中,並沒有人我之別,物我之分。要證到這個境界,只有當我們放下虛妄不實的自我觀時,才有可能。
身與心是分開的,卻互相依存,身心相互依存是人類的特質,身體帶著心到處跑。雖然無色界的眾生沒有像人類一樣的身體,這點稍後會論及。很不幸的,我們的心必須依賴身體。如果我們的身體非常疼痛,心馬上會變得煩燥、消極、厭惡或抗拒。如果感到很快樂,就會產生執著,想抓著不放。身體的感受會引起心理反應,然而,並不一定永遠都是這樣。佛陀經常說:未覺悟的人被兩種東西所困擾:身與心;而覺悟的人只被一樣東西所困擾:身體,因為覺悟者的心不再對外境有反應。我們有可能不受身體影響,然而對我們這些尚未開悟的眾生而言,身與心仍然要相互依存。
當我們觀察身體的四大元素時,我們是觀察身體的結構;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從四方面來觀察心。在觀察時,我們會發現:事實上身體並沒有主宰者。首先是觀察感官意識(sense-consciousness),也就是看、聽、嚐、觸和嗅等五種感官;其次是觀察由感官接觸所生起的感受(受蘊),包括樂受、苦受和不苦不樂受;第三個步驟是觀察心的認知作用,也稱為標明(labeling)作用,例如,當苦受生起時,心中所標明的是「痛苦」;第四是行蘊(mental formation),或反應;心感到痛苦時,一般的反應是:「我不喜歡」或「我一定要把它去除。」在這個階段,能夠覺知心的四個方面,觀察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感官接觸、感受、認知和反應,這對我們的禪修非常有幫助。無論在禪修或在日常生活中,知道心的四個層面是非常重要的。佛陀教我們:要知道心的四個層面,對所了知的經驗要有智、見,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身與心中根本沒有「我」。「我」只是一種想法,一種觀念,它深深的烙印在心裡,我們周遭的人全都如此認為。
然而這個「我」不只是一種觀念,它也能夠引起貪與嗔,我們知道貪與嗔非常容易生起,我們與貪嗔共住,熟知貪與嗔,而貪與嗔無法引起快樂。修行時,我們不但要觀察身體的四大,也要從四個層面來觀察心,觀察心念如何生起和消失。我們可以觀察每一次的感官接觸(一種味道、香味),也可以觀察「觸」如何引起感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等。
大部份的人都能覺察到第一步和最後一步-感官接觸和隨後生起的心理反應:「這個看起來不錯,我要這個。」或是:「這個不好,我不要。」心理反應是如此的快,以致於我們完全忽略了認知(想蘊)和反應(行蘊)兩個步驟。正確的修行方法是:一旦觀察到有心理反應,馬上要回想它是感官接觸所引起的;再去觀察心的感受,這種感受是感官接觸所引起的;然後再去觀察心如何詮釋-也就是心的標明作用,如骯髒、噁心、可口、無聊等;觀察這兩個錯過的部分:感受和標明。現在,在心的四個層面中(即感官接觸、感受、認知和反應)去找出是誰在感覺(senses)、感受、認知和反應。心會告訴我們:「是我在做這些事。」然而這種「假設的我」只是一種觀念而已,哪來的「我」在做這些事?我們會發現:這四個層面是自然而然,根本沒有「人」在做這些事,而我們可以觀察它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可以在這四個層面中的任何一點停止,尤其是在「認知」(標明)時,若在「認知」這個階段停止,我們會發現我們對外境可以沒有反應。然而,當我們這樣做時,心會說:「是我在做決定,是我決定這樣做的。」現在,你可以去找這個「我」,只找到「決心」而已,而這是一種心理現象,並沒有「我」在裡頭。我們要一再觀察,因為在五蘊中隱藏著假象,即「我」的存在。有人認為這決心來自於他們的思考;有些則認為來自於他們的感受;其他人會認為來自觀察者或是意志力(willpower)。我們可以自問:當心沒有反應,沒有觀察者,沒有意志力時,這個「我」在哪裡?當這些「我的」(指感受、意志力等)不存在時,「我」又在哪裡?在做什麼?要了解究竟實相,必須有專注力和意願,才能了解生命的最深層,而不是只探究表面的現象,如喜好或厭惡等。如果我們有長期喜好的與厭惡的事物,或許我們可以找到超越喜歡與厭惡的解決之道。
在出定後,這種觀察很有用;如果不禪修,可能會流於知性遊戲(intellectual exercise),而心為了逃避這些問題,會樂於這種遊戲,心不想觀察,並急著告訴我們:「是的,對的,這樣就好了。」如果我們只觀察膚淺的層面,沒有什麼益處;相反的,當深入觀察而導致開悟時,它的益處是非常大的,也就是類似「啊哈」的經驗。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要認為有一個「我」在修習,是「我」在說「啊哈!」;恍然大悟的是心,不是「我」。
佛陀以譬喻來說明在四禪所生起的觀智:
譬如琉璃寶珠,美麗出色,八面玲瓏,磨治瑩明,明亮無瑕,具一切美相,以索貫之,索深青色,若深黃色,若赤紅色,若純白色,若淡黃色,有目之士,置掌而觀,當知此琉璃珠…。比丘亦復如是,心寂靜純淨,無有煩惱,離隨煩惱,柔然將動,而恆安住於不動相,以心傾注於智見。彼知是事:我身由色成,四大種成…,我之意識依存於此,與此關聯。
觀智如同一塊完美無瑕的寶石一般,清澈、明亮、沒有瑕疵。正如欣賞寶石需要好的視力,而要有觀智則需要一顆純淨、專注的心。禪修時,所觀察的對象必須和自己的內心有關。是心在觀察:「誰擁有感官觸覺?是誰在反應?」當我們觀察時,必定與我們的內在感受有關,內心會一再的認為:「是我!」當我們如此認為時,我們應該進一步觀察,雖然確實有這種想法,當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這種想法是不合理的,這是錯誤的觀念。如果我們真的想知道真相,就要繼續觀察四大,觀察身體生起的原因和身體是無常的,觀察我們必定會死去,觀察身體的一種特質或所有的特質(指無常、苦、無我)。當心的四個層面按照次序生起時,我們也要觀察這四個層面:「是誰在做這些事?為什麼所做的常常與所希望的相反?為什麼我想進入四禪,卻發生這種事?」
用這種方法,我們會慢慢了解佛陀所教導的法。如果我們只停留在表面現象,我們將永遠無法應用這些修行指導。佛陀說:如果我們能走完整條解脫道,就可以徹底解脫苦。在修行的過程中,我們對佛陀所說的法會越來越有信心,也會依照他的指導繼續我們的解脫之旅。
第七章:五禪、六禪
-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
西元五世紀,覺音論師(Buddhagosa)在《清淨道論》中,為前四個禪那做了很貼切的譬喻:
有一個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他沒有帶水,感到越來越渴。終於,他看到遠處有水池,他非常興奮,充滿喜悅。
「在沙漠中旅行,沒有帶水」並「感到越來越渴」指我們的內心追求喜樂、幸福及平靜,這些是無法從外境獲得的。「看到遠方有水池,非常興奮,充滿喜悅」類似在初禪所體驗到的感受,知道目標在望,雖然仍在遠方,但很快就會到達目標。
後來,那人站在池邊,知道這池水能除去口渴,感到非常歡喜。這是描述二禪的境界,我們知道自己已經到了內在滿足的邊緣(brink)。然後,他走到水池,盡情喝水,感到非常滿足,和剛才到處尋找池水的心境相比,是完全不同的,這是三禪的體驗。如果我們很長的時間沒水喝,我們知道此時身心是多麼苦惱。這個譬喻道出我們的心理和情緒:在追求所渴望的東西時,內心總是煩躁不安。一旦找到我們所渴望的東西,那種心境可說是天壤之別,我們感到喜悅、滿足。這種喜悅的心境不是佛陀所說的最終目標,但也只差一步。然而,這是極其重要的一步,因為我們可以從中獲得繼續修行的動力,以及獲得新的內觀智慧。
現在,這位在沙漠中的旅人感到非常平靜。之前,為了生存,他不斷尋找水源,感到焦慮不安,他的口渴使他到處尋找水,現在,口渴已經解除,他走出水池,在樹蔭下躺著休息,從困頓中恢復過來。這種輕安和四禪的經驗一樣,不是睡著,而是完全的寂止,讓心休息。
以上的譬喻反映了我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有時,我們無法覺察所發生的事。正如我們要生存離不開水一樣,要使內心滿足,也離不開喜悅和平靜。我們無法覺察自己不停的在追求某些東西。心的掉舉反映了這點,我們到處攀緣,結交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觀念,嘗試不同的工作。無論我們想做什麼,都反映出內心的渴求,我們希望能從外在的物質來滿足這些渴求。其實,我們所追求的就在心中,所以要解決內心的渴望,也只能在心上下工夫,而且快多了,因為這是我們能找到滿足與喜悅的唯一所在。
四禪是進入無色界禪(the formless jhanas)的跳板,我們都有進入四無色界禪的能力,事實上,這些定境或可稱為「平凡無奇」,雖然這不是開悟,卻是開悟的基礎,並能訓練我們的心力。開悟不是簡單的事,需要極大的心力,所以我們必須先打好基礎。修習禪那需要耐心和堅忍不拔,最重要的是,要有無所求之心(not looking for any achievement or result)。
前四個禪那是色界禪,也有「微細物質禪那」 的意思,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類似的境界,雖然物質生活並不圓滿,而且必須依靠外境。我們都有類似色界禪的體驗,因此
比較容易了解這些禪那。所有這些定境(absorption states)都潛藏在心中,只是被我們的顛倒妄想和不斷生滅的念頭所障蔽。無論何種念頭生起,「我是否必須入定」或「我必須做這」或「我不想做」,這些念頭是沒完沒了的。這些「定」被我們的念頭、情緒、反應、意見和觀念所障蔽,這些我們所熟知的心理現象會障礙我們入定,直到我們了解,我們從不曾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滿足,我們才會在禪修時把它們放下。當「我」喜歡或不喜歡某些東西,或是「我」想要有所成就或不想有成就。這些念頭對禪修毫無意義,我們必須把這包袱丟掉,心才會轉到其他心識狀態,這是佛陀向布吒婆樓解說的內容。我們都有意識(consciousness),因此都可以進入這種禪定的境界。
有關禪定的論述和言論有些是矛盾的,讓人產生困惑。看了一些有關禪修的書籍,容易先入為主,會產生成見,妨礙禪修,所以沒有接觸任何禪修的論述反而更容易禪修。只要坐下來,放下心中的罣礙,心自然會靜止下來,沒有顛倒妄想,直到證入涅槃,讓心體會涅槃之樂。在這之前,只要放下一切,心就能體驗禪那的境界。我們甚至不說是「入」定,而是把各種念頭放下,就像一隻從水池裡跳出來的狗,把水抖落一樣,我們也把念頭從心中抖落。
下一步是無色界定。初禪到四禪是色界禪那(rupa jhanas),接下來的是四種無色界禪那(arupa jhanas)。Rupa指形相(form),Arupa中的A指「非」或「不是」。這四種禪那是無形無相的,在日常生活中,在一般的心識狀態下,不可能有無色界禪那的體驗。事實上,未曾禪修的人會覺得這有點像神話,而禪修者即使沒有無色界定的體驗,也會有粗淺的了解。就像前面的篇章中所說的,前四個禪那和身體的感受或情感有關,而佛陀所舉的譬喻全與身體有關,如佛陀提到全身遍滿、沉浸在喜樂中;而在四禪,身體處於寂止狀態,這都和感受有關。而無色界定,只有心境(mental states),沒有任何情感或身體的感受,所以經中沒有任何譬喻。禪修者要證入這種禪那,平日必須不斷修習前四種禪那,直到心變得溫順、柔軟、有彈性,不再頑固和抗拒,才能體驗更高層次的無色界定。
佛陀是這樣敘述五禪的:
復有比丘,超出所有色想,滅除障礙想,不起異想(perception of diversity),故達空間是無邊的空無邊處定,因此先滅色想,同時生起空無邊處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惟有空無邊處定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在四禪,我們不再有身體的感受,只覺察到心、感情、感受的寂止,所以到了第五禪的「超出所有色想-身體的感受」,我們毋須刻意去修便可以做到。而破除「障礙想」(all sense of resistence)就要刻意去破除才會成功。最重要的是,我們會以皮膚為限的身體為「我」,皮膚以外就不是「我」了,我們都很清楚自己所佔的空間大小,這是我們強加在自己身上的自我限定。在前四個禪那,這種「界限」已經被擴大到某種程度,不再以身體為限,至少,禪修者的思想觀念不再僵化。
從四禪退出,如想進入「空無邊處定」,我們可以觀察當時心所感覺到的身體邊界,並慢慢把它擴大。前面章節所提到的觀四大,其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佛陀說;「不起異想」 ,意指我們必須超越個體(singleness),如一個人、一間房子、一棵樹、一座森林、一片天和地平線等。我們將事物視為個別的、有範圍的,這種「異想」是人類的自然心態。巴利語papabca意為差異(diversity)或各式各樣的。每一種物種都由無數的個體組成,人類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的外表看起來有點不同,我們被這些差異,被不同的面孔所吸引。在森林裡,我們欣賞
每棵樹的形狀,看看樹幹或樹葉,觀察每棵樹獨特的地方,並感受它的美。同樣的,我們也會仰望天空,欣賞明月和看單獨的星星;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來觀察人,我們被某個臉孔所吸引,發現它是討人喜歡的,或對某人感到厭煩。然而如果要進入空無邊處定,就必須超越所有的個體及其差異。
有兩種進入空無邊處定的方法,我們可以同時用兩種或只用其中一種,至於要用哪個,視我們在擴大心識時遇上多少困難而定。第一種方法是先觀察身體的邊界,再將這邊界慢慢擴大到無窮盡的空間。假如在這個過程中遇上障礙,意識無法擴展,那麼可以用第二種方法:觀想森林、草原、山川、河流和海洋,再觀想整個地球和天空,以及地平線,當我們觀察到地平線時,再把它們放下,只剩下無盡的空間,這就是所謂的「不起異想」。
去思考這些指導方法,看看佛陀所說的是否真實不虛也很有幫助。界限是真實存在的抑或只是光學上的幻象?從科學的觀點來看,宇宙間根本沒有固體粒子,只有不斷離合的能量粒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往往聽過就忘了。透過觀察,我們知道事物的真相,也知道所有的界限都是心製造出來的,因此會放下對「異想」的執著。
佛陀所說的進入「空無邊處」的兩種方法是可以刻意去做的,毋須等待好運來臨。透過修持空無邊處定,心會擴大,大部份的人從來沒有這種想法,即使是透過實驗和研究而了解真相的科學家,也無法使它成為他們思想過程(thought processes)的一部分,只把它視為科學上的真相而已。然而,如果這是真理,那麼這指我們的心,因為心是宇宙最根本的因素;當然這裡的心不是指個人的、我們所熟知的心。一般人將自己的心侷限於個人,無法觀察到宇宙的真相;透過思考和禪修,我們可以把心擴大。心的侷限越少,我們越能把心擴大,也越容易證到究竟實相。
通常我們所知道的與究竟實相無關,這種認知障蔽和扭曲了我們對究竟實相的了解。如果我們把心擴大,就能超越這些界限,我們都有這種潛能,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潛能發揮到極致,不要把自己侷限在框框裏,要盡可能的把心擴大。
在修習止禪後,尤其是任何禪那(jhanas)後,我們應該修習內觀-智慧禪,這會有很大的利益。
在接下來的篇章中,佛陀開始討論當時社會流行的四種錯誤的自我觀。我們不要認為以下的古典經文和現代人毫無關係,事實上,佛陀所說的正是現代人所想的。
今有沙門或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此我為有色,四大所成,父母所生,而身壞時,斷滅消失,死後無存。於是此我,全歸斷滅。」
布吒婆樓也有同樣的看法:認為自我就是人的身體,身體就是我。這種觀念在現代是如此流行,有此觀念的人多不勝數,在任何有關神祕經驗的雜誌都會發現,有這種觀念的人相信,只要使身體變得完美,我們就是完美的人。然而,我們不可能使自己的身體變得完美;其次,即使擁有完美的身體,而身體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我們只是覺得身體好了些,僅此而已。
一般人當然不會談到地、水、火、風這四大元素,但所想的內容都是一樣的。每次照鏡子時,我們都會說:「這是我。」鏡中人除了是我外,有可能是別人嗎?我們經常看到鏡中的「我」,且認定這就是「我」,這種想法是障礙想,會侷限我們。身體從來不會真正滿足,相反的,身體的慾望需要不斷的滿足,有時還會有頗荒唐的需求。我們的身體給我們帶來許多麻煩,想想看如果打坐時,坐在坐墊上的只有心而沒有身體,那會省了多少麻煩,禪修會變得多麼美妙,從
此背不再痛,腿不再麻,身體不再癢,不再打噴嚏。當然我們仍要專心,不過容易多了。這個身體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個大包袱,而我們竟然把這個包袱當成自己,我們知道這個執著是多麼荒謬嗎?為甚麼我們要像布吒婆樓和他的朋友一樣視臭皮囊為自我?
接下來是另一個錯誤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聽起來似乎更偉大(grandiose):
或有人於此,作是說言:「汝所言我,斯我實存;予決不謂,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斷滅,猶有他我,是天有色(軀體),屬於欲界,養以段食。汝不知不見,予能知能見。此我身壞,斷滅消失,死後無存,於是此我,全歸斷滅。」
這種看法是將靈魂視為自我。當身體壞滅,這個「我」就消失了,但仍有另一個屬於欲界的神我(divine self),在理智上我們可能不相信有這種神我,不過心裏卻懷疑可能有另一個自我在靈魂裏,或有個靈魂在自我中。不論是哪種看法都和視身體為我大不相同。而靈魂我(soul-me)或許是好的,我們不承認我們有善惡兩面。有些人認為靈魂是比較完美的,所以才是自我。即使我們在理智上否認靈魂為自我,內心卻渴望:如果身體不是自我,至少自我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另一種見解是,不論人死後到哪裏,自我都會快樂。
第三種錯誤的觀念是:
或有人於此,作是說言:「汝言之我,斯我實存,予決不謂,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斷滅,猶有他我,是天有色(軀體),由意念所生,具足四肢,諸養無缺。汝不知不見,予能知能見。此我身壞,斷滅消失,死後無存,於是此我,全歸斷滅。」
這段經文說的是由意念所生、微妙的、更高的
自我,不是靈魂,在印度教稱為「梵我合一」。梵我(Atman)是絕對的自我,而非特定的自我。佛陀指出它的嚴重錯誤,並一再說明這些觀念是錯誤的。這個「意所成我」(mind-made self)指的是較高的禪那經驗,第一個是空無邊處定,在這個禪那,心體驗了無盡的空間,產生「我」融入空間的概念,所以說是心在製造自我。
所有「自我觀」的產生,是因為我們無法放下一個觀念,也就是在各種行為的背後,一定有「某人」在行動。我們會想:「是誰在做我所做的事?」會自問:「是誰在想我所想?是誰在反應我的感官接觸?是誰想要我要的東西?一定有人在作主。」即使我們不再視身體為自我,要做到這點並不難,我們也會去找其他的自我,首先是視靈魂為自我,其次是執取超然的自我,或是把無色界定所體驗到的心識狀態視為自我,如空無邊處定或識無邊處定。
第四種錯誤的自我觀是:
或有人作是說言:「汝言之我,斯我實存。予決不謂,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斷滅。猶有他我,超出一切色想(bodily sensations),滅有對想(all sense of resistance),不起異想,故達空是無邊之空無邊處。汝不知不見,予能知能見。此我身壞,斷滅消失,死後無存。於是此我,全歸斷滅。」
這是共相之自我(self within unity)。如能進入第五禪,就能體驗到無邊的空間,以及統一的境界,此時,沒有間隔,沒有阻隔。當時流行的統一意識(unity-consciousness)其實也有部份屬實。這種意識是指我們在觀察時,不會執取觀察者的意識為自我,意識好像旁觀者一樣,觀察所發生的每個現象。如果我們視觀察者為自我,我們就會視色身、靈魂或超然的我為自我,我們就會變得愛評論挑剔和厭惡某些人事。我們會被慾望所困,因為我們會希望能得到我們所觀察的某些東西,或想擺脫某些事物。一旦有這種觀念,我們就會視色身為自我,相信有靈魂或超越的自我。當我們有融合的經驗,我們會認為已經將自我意識(ego-consciousness)除去,這就是與神合一的觀念,或是印度教中的梵我合一。佛陀反對這個觀點,因為「合一」表示有某人或某物進入這種合一的狀態。
以上四種錯誤的自我觀,仍然有一些「自我」的假象。而統一意識比獨立意識(separation-consciousness)有價值,因為在統一意識中,我們能感受到慈心與悲心,因為如果眾生皆是一體,有誰能惱害或激怒我們呢?此時,也去除了許多憂懼。當我們感到孤立時,才會有被周遭的人威脅的感覺,甚至畏懼死亡。當我們與萬物合一時,無論我們稱之為神我合一或梵我合一,或其他的形容詞,我們的畏懼感會大為減少。然而仍有些許的自我感,是這種自我感與更高的理想(higher ideal)合一。
以上四種錯誤的自我觀值得我們去深思,看看自己是否執取其中一種:我們視身體為我?靈魂為我?超然的我?與萬物合一的我?我們的自我觀是哪一種?或許我們永遠無法體會統一意識,但我們會思考這種觀念,並反問自己是甚麼和甚麼合一;我們可以觀察是否身體內有靈魂,是否有「我」;我們可以觀察身體與超然的自我,這種自我有甚麼依據?我們錯誤的自我觀是如此根深蒂固,所以當心是偏狹的,不是溫順、開闊的,根本無法觀察實相。因此我們很難相信:這些錯誤的自我觀只是支持自我存在的理念而已。
當我們不再需要或不再希望我執(ego assertion)繼續存在,觀察實相就容易多了。觀察實相越清楚,就越容易禪修,因為我們知道「自我」是禪修的唯一障礙。「自我」只是一種觀念,我們越了解這點,「自我」就越不會阻礙我們修行。
佛陀的教法不只是心理輔導之類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去思考,繼而以全新的方式去體驗人生,這是為何佛教能綿延二千五百年而不消失的原因。心理學界不斷有新的學說出現,而佛陀的教法是歷久彌新,不可能有新的理論產生。當我們在修行時,我們應該試著去了解佛陀的教法,所以要有觀察和思辨的能力。
在修止禪時,我們試著平靜和專注;在修觀禪時,我們如實的觀察不同的現象,止禪和觀禪應同時修習。從經典中我們知道佛陀的教法是完整的,我們不可以只選擇一部份來修,而忽視其他的,這樣是無法解脫的。所有修行的方法包括:持戒、守護諸根、知足、正念正知、修習止禪與觀禪,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接著談到第六禪:
復有比丘,超出所有空無邊處,達「識是無邊」之識無邊處,因此先滅空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起「識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識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此段經文有關無色界定的解釋非常簡要,或許是布吒婆樓的程度還不夠,或是有關的解釋遺失了。
在第五禪,我們體驗到空無邊處,現在要做的是,將注意力由無邊的空間轉向觀察空間的意識上。要觀察無盡的空間必須有無盡的意識。從第六禪出定後,我們會自問:「我從中學到了甚麼?」我們知道個人是不存在的,只有整體(unity)。一旦接受了這點,統一意識便會生起。無論是在空無邊處定或在識無邊處定,我們都找不到有個人在入定,如果有,那就不是這兩種定了,因為有個觀察者在裡頭。在四禪,觀察者縮到最小,這使心力大為提升,變得很清明。在第五和第六禪那,出定後,觀察者充分了解,除了無盡的空間或意識外,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東西。
我們有了識無邊處定的經歷後,就會了解它是普遍意識(universal consciousness)的同義詞,一旦我們知道:我們都屬於普遍意識的一部份,就不會以任何不善的念頭、語言或行為來污染普遍意識。我們都在普遍意識中,我們的意識
越純淨,也越容易感受到純淨的普遍意識。在普遍意識裡,有各種念頭,無論我們想甚麼、說甚麼或做甚麼,都在普遍意識裡,而且不會消失。
我們將五禪、六禪來和初禪、二禪比較,當我們有快樂的感受,喜悅也會生起。我們要做的是將注意力從感受轉向情緒,這些感受和情緒已經存在,我們只需覺知。從五禪到六禪也一樣,只是比較微細。有了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會同時生起,我們只需把注意力從無盡的空間轉到觀察這空間的意識即可。
「識無邊處」很容易被誤解,特別是印度教把它視為修行上的成就,這種體驗的確使人認為:「我就是那(I am that)」,梵文是tav tvam asi,也是用來形容統一意識。中世紀基督宗教神祕學家艾克哈(Eckhat)用了不同的術語:「上帝與我是同一的。」當時他幾乎被處以火刑。我們猜測他可能進入高層次的禪那,除此以外,無法解釋為何他會說出這樣的話,因為如果他最大的努力(endeavor)不是想成為某個特定的人,很明顯的,他說這話不是出於自傲,而是謙卑。
識無邊處定是證悟和禪修的一部份,透過修行,當我們有了這種禪定,心也會越來越清明,越能觀察實相,心不再偏狹,不再自我設限只關心特定的我。透過禪修,甚至可以超越「絕對自我」(absolute self)。從空無邊處定和識無邊處定出定後,我們會發現苦仍然存在,修行仍未結束;只要心中還有自我,這個自我必定有苦。所以觀察我們所認同的是哪一種「自我」是非常重要的,並自問:為何會有這種自我觀。當我們發現這些自我觀並沒有根據時,我們的認知會發生重大的改變。
第八章:七禪、八禪、九禪
-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定、滅盡定
世尊復言:「布吒婆樓,復有比丘,超出所有識無邊處,達『所有皆無』之無所有處,因此先滅識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起無所有處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無所有處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這段有關七禪的描述和先前的一樣簡潔。英譯者將無所有處譯為no-thingness,這種翻譯比較明確,讓我們更能了解這個層次的禪那,否則我們很難想像如何觀察「無所有」(甚麼都沒有)。
第五、第六和第七禪經常被稱為毗婆舍那禪(vipassana jhanas)或內觀禪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從色界的四個禪那證得內觀智慧。
再扼要重述一遍:在初禪,心中已有我們想從外境追求的境界;在二禪,我們從禪定中所體會的喜悅是感官接觸所無法產生的;在三禪,當我們無願無求時,心自然會知足、平靜。值得一再強調的是,要進入禪那,必須放下所有的感官欲望,包括放下想入定的願望,若放下,便可以入定;在四禪,當自我變小時,寂止會生起,隨之而來的是平靜的心(even-mindedness)或捨心。
在五禪及六禪所生起的觀智(insight),發現自我消失了,只剩下空間和意識。雖然有觀察者,卻找不到觀察的「人」,因為觀察者已經擴大到無盡的空間和意識。現在坐著正在讀書的小小的觀察者,根本無法體驗到「無限」,而「無限」卻可以在禪那中體會,觀察者也可以擴大到無限。此時雖然有意識,這是心,沒有「人」在那裡。
在七禪,在無所有處,我們知道不但沒有「人」,也找不到任何物體。同樣的,在五禪(空無邊處)和六禪(識無邊處),沒有任何物體可以執取,因為在整個宇宙中,根本沒有可以執持的堅實物體。這些有關禪那的體驗聽起來很有趣,做起來是另一回事。有了禪那的體驗後,我們有了內觀智慧,因此對人和對世間的反應會改變,我們知道那些看似堅固的物體,事實上是不斷變遷的。
七禪有兩種不同的體驗。我們可以覺知到非常微細的活動,一種粗略的比喻是:就像看著泉水不斷流動一樣。另一種體驗是,我們覺知到廣袤的空間,也就是無盡空間和無盡意識的合而為一,在這廣袤的空間裡,無一物可得。
要證得甚深的內觀智慧並非一蹴可躋,要花時間,要一再證入不同境界的禪那,才能證得智(knowledge)與見(vision),才能應用自如,然而,這個境界不是涅槃,只是證入涅槃的過程。
布吒婆樓,比丘已達調御之想(controlled perception),彼由前至後,次第以達想之極致。
「調御之想」指禪修者在禪修時,首次能控制自己的心。有些人認為他們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果真如此,我們決不會愚笨的讓自己不快樂。「調御」意指我們可以想一些我們所選、所喜歡的去想,並放下那些對我們修行的目標和快樂無益的事。當心專注一境,進入禪那時,便知如何調御自己的心。很明顯的,越高的禪那,調御的能力也越強,在三禪,禪修者的「調御之想」才真正開始。佛陀說:隨著定力加深,我們一步步的邁向想之極致(limit of perception)。
「想之極致」是八禪的境界,使心能休息最久,使心充滿精力,這是心進入第九禪那「滅受想定」(滅盡定)前的最後階段,這就是布吒婆樓在第一章所問的「識最究竟的滅盡境界」。「增上想滅」的巴利文是abhi-sabba-nirodha。Abhi 意為「增上」;sabba是想(perception);nirodha是滅。經中記載,只有不還者(阿那含)和阿羅漢才能進入這種禪那。
某些論著詳細描述九禪:進入滅盡定的人好像死了一樣,因為呼吸如此微細,以致於難以覺察,然而仍有生命力,仍有體溫及微弱的心跳。據說禪修者可以進入滅盡定達七日之久。通常,不需要入定這麼久,故此舉被認為是禪修者想展現其定力,這是佛陀反對的。
…處此想之極致時,彼作是念:「思慮(mental activity)之事,於我為惡;不思慮事,於我為善。」
這裏提到念頭本身便是苦,這是很重要的內觀智慧。任何心的活動-希望或欲望都是苦,因為有念頭,心就會動,心動就會煩躁,煩躁會產生苦。,由於慾望永遠無法滿足,因此苦也無法斷除。例如,我們對過去的某些事情不滿,希望有所改變,無謂的煩惱便隨之生起。我們應該把「過去」放下,苦自然會消失。現在,我們正在修行,能利益我們的想法是去想如何解脫,而毋須去想過去的事。同樣的,如果我們想著未來的事情,無論想得到某些東西,或希望某些事情不會發生,結果一樣會產生苦。當我們真誠的面對自己時,就會發現我們經常犯這種錯誤,而這是那麼愚痴!
「思慮之事,於我為惡;不思慮事,於我為善」並不是要我們像植物人一般沒有思慮。佛陀擁有最敏銳的腦袋,以極高的智慧去解釋人類的處境。這句話的意思是告訴我們,在禪修以外的時間,有許多念頭是多餘的,這時候只要覺知呼吸、動作、景像和聲音即可,不需要思考。透過禪那,我們學到如何注心一境,排除妄念,如果我們每天都這樣修習,心就會更有力量,不會過勞。
設我仍有思慮意欲,我之想(perception)雖得消滅,而餘粗想,將復再生。我今寧可不起思慮,不起意欲。
禪修者知道:在七禪及八禪所生起的隱約的「想」,會隨著念頭的生起而消失。與禪那的心境比較,平常的念頭比較粗糙,尤其是不好的心境,如自我投射的作用,也就是把內心所想投射到他人身上,並責備所投射的對象。自我投射的人不會承認他人的壞處事實上是自己投射的。當然,在這個世間,我們必須有工作,必須交談,這時的心是粗的,佛陀也不例外。在這部經中,佛陀以一般層次的心才能和布吒婆樓交談,並回答他的問題。然而,我們要知道「想」雖有粗細之分,而微細的「想」會為心和生命帶來優良的品質,我們可以說:我們就是我們所想(we are what we think),所以我們要仔細觀察自己的心念和選擇所想的內容,越仔細觀察,便越容易修習禪定。
彼於是不起思慮,不起意欲。不起思慮,不起意欲已,其想即滅,餘想不生,而達於想滅。
Imagine可譯為想像或幻想。由於巴利文是沒有人說的語文(dead language),所以不容易翻譯。當我們不起思慮,不起意欲,不再計畫,不再反應、投射,那麼比較粗的心便不會生起。世上一切的分別,包括喜歡與不喜歡,認為他人應該做或不應做,這些念頭不再生起。只有當我們完全放下,禪那中比較微細的「想」才會生起。
佛陀接著說:
…而彼之想滅。布吒婆樓,如是次第而至增上想滅智定。
在這裡,佛陀並沒有詳細解釋八禪-非想非非想處(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此時,心處於沒有活動的狀態,觀察(observing)幾乎完全停止,但又不是完全沒有覺知,所以不可以說有覺知,也不可以說沒有覺知。在九禪(滅受想定),即使是三果(不還者)聖人,仍有些微「我」的感覺,尤如芳香之於花一般;只有阿羅漢的滅受想定完全沒有「我」的感覺。
佛陀接著說:
布吒婆樓,汝曾聞如斯次第增上想滅智定否?
否也,世尊,吾今唯知世尊所說,謂:「布吒婆樓,比丘已達調御之想,彼由前至後,次第以達想之極致,處此想之極致時,彼作是念:思慮之事,於我為惡;不思慮事,於我為善。設我仍有思慮意欲,此想雖得消滅,而餘粗想,將復再生。我今寧可不起思慮,不起意欲。彼於是不起思慮,不起意欲。不起思慮,不起意欲已,其想即滅,餘想不生,而達於想滅。布吒婆樓,如是次第以達增上想滅智定。」
「布吒婆樓,實如是也。」
布吒婆樓是個好學生,他記得佛陀所說的話。現在,他的問題終於得到答案了,他又有另一個問題:
世尊,世尊說示,想之極致(the summit of perception),為一為多耶?
佛陀答道:
布吒婆樓,吾所說示,想之極致,亦一亦多。
布吒婆樓接著問:
如是世尊,云何說示,想之極致,亦一亦多耶?
佛陀回答說:
布吒婆樓,實如是如是達於想滅,如是如是現想之極致。布吒婆樓,故吾說示,想之極致,亦一亦多。
如果我們不用想(perception)滅,而用識(consciousness)滅,就比較容易了解佛陀的意思。在初禪,「識」有所轉變,並非變得非常微細,而是有所不同。一旦出定,我們的識-想之極致便停止。隨著定力加深,「識」變得越來越微細,直到我們達到最後的「想之極致」,也就是心的極限,接著進入滅盡定。佛陀的教導很有次第,他不但教我們最高層次的「想之極致」,也將每一階段的頂點告訴我們。布吒婆樓仍不滿意:
世尊,先有想生,而後智生耶?先有智生,而後想生耶?抑或智與想,非前非後而生耶?
佛陀回答:
布吒婆樓,先有想生,而後智生,實由想生,而智生起,故知:「實由此緣(conditioned)故,於吾生智慧。」
在第六章我們討論過心的四個層面:意識、感受、想和行。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的因果關係,在智生起前,「想」必先生起。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有經驗,智才會生起。不只修行如此,所有事情都是如此,例如,要了解無常,我們首先要觀察呼吸或念頭的生滅;要了解在禪那時的心識狀態亦然,禪修者必須先有體驗,然後才能「知道」所經歷的過程。巴利經典將佛陀此處所說的「智」形容為省察智(reviewing knowledge),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有經驗,之後才能省察。事實上,透過對經驗的了解,內觀智慧才會生起。我們都有開悟(enlightenment)的種子,如果對我們所體驗到的事物沒有真切的了解,就無法獲得內觀智慧,也無法開悟,這是佛陀的教導中很重要的部分。
佛陀接著說:
布吒婆樓,可知依此理趣,先生想,後生智,由想生,故智生起。
在這裏佛陀直接回答布吒婆樓的問題。很明顯布吒婆樓對此頗感與趣,卻不熟悉禪那的境界,不然就不會問這些問題了。他又問了另一個問題:
世尊,想即人我耶?抑想與我(self)為異耶?
從相對的層次(世俗諦)來看,一定會有困難。人們視「想」為我。如果正在想的不是我,那麼是誰在想呢?一定是「我」。我們的念頭不停打轉,就永遠找不到答案;如果想要解脫,我們必須先放下所有的思想、觀念。同樣的,布吒婆樓也陷入世俗諦中,我們很容易認同他的看法,因為我們也有同樣的觀念。
佛陀想使布吒婆樓放棄「我」的錯誤知見,所以問布吒婆樓:「布吒婆樓,汝以何者為我?」布吒婆樓回答:
世尊,吾自思惟,粗我(gross self)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養。
布吒婆樓把身體視為我。佛陀回答說:
布吒婆樓,汝之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養。布吒婆樓,設若真實,則汝想與我,實非一物。布吒婆樓,由此差別智,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吒婆樓,如是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養。但於此人,猶有此想生,他想滅。布吒婆樓,由此差別,可得而知,想、我非一。
如果布吒婆樓的粗我(身體)是他的自我,那麼他又如何說明「想」呢?想不斷的生滅,如何可能和身體同一?布吒婆樓似乎承認這點,但又有另一個想法:自我是由意念所生。我們可能有同樣的看法。人們經常說:「我不是身體。」這句話太突兀,比較有深度的看法是:「這個身體不屬於我。」如果我們說:「我不是身體」,這暗示了擁有權,而誰是擁有者呢?當然是我囉。「我」擁有身體,「我」想保持身體健康,為它帶來快樂的感官接觸。身體屬於我,正如屋子、車子、冰箱屬於我的一樣,這是布吒婆樓的看法:
世尊,吾以我為意所成(mind-made self),肢節具足,諸根圓滿。
他仍不放棄「擁有權」的想法,只不過以「意」(mind)代替身體,「我是意所成」而不是「我是身體」。佛陀回答說:
布吒婆樓,汝之我為意所成,肢節具足,諸根圓滿。布吒婆樓,設若真實,則汝之想與我,實非一物。布吒婆樓,由此差別,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吒婆樓,若我為意所成,肢節具足,諸根圓滿,然於此人,猶有此想生,他想滅。布吒婆樓,由此差別,可得而知,想、我非一。
布吒婆樓不得不面對真相,於是又想出另一個論點:「世尊,我以我為無形,而想所成。」事實上,布吒婆樓相當聰明。如果「自我」不是人的身體,又不是心,可能是某種無形無相的東面。「無形無相」(formless,無色)是佛陀敘述較高層次禪那的用語。佛陀再度告訴布吒婆樓:「想」是一回事,而「自我」是另一回事。假設有一個無形的自我存在,也不可能是想,因為「想」會不斷生滅,所以想不可能是自我,佛陀試著讓布吒婆樓了解這點。布吒婆樓又問道:
復次,世尊!人我(a person’self)即為想耶?抑想與我為異耶?斯義吾可得知否?
佛陀回答說:
布吒婆樓,人我與想為同一耶?抑想與我為異耶?汝欲知此,甚難甚難,以汝依他宗見,有他宗信仰,持他宗所期,以他宗之學說為歸,以他宗之行持為旨故。
佛陀的意思是,你不是我的學生,你向其他的老師學習,有不同的信仰,受不同的影響,所以要了解這些道理是非常難的。我們也一樣,如果我們相信有靈魂,相信往生後會快樂,或接受其他的修行方法,就很難了解。當然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心,我們經常如此,但要看有沒有必要去改變。要了解佛法,我們一定要覺知自己的苦(這是第一步),最後我們會發現,以前的方法無法根除苦,或許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才會徹底改變。
雖然後來布吒婆羅成了佛陀的弟子,但此時的他,仍滿腦子的觀念和理論,這些理論和觀念是他從不同的老師聽來的,或來自古代婆羅門的《梨俱吠陀》(Rg Veda),他們認為要透過記憶來修行,這些是布吒婆樓非常熟悉的。佛陀很溫和的指出,布吒婆樓以前所學的障礙了他,使他無法了解佛陀的解說。結果布吒婆樓也放棄這些問題,不再提問,他們的對話到此告一段落。在下一章,我們會看到布吒婆樓有完全不同的問題。此時,他是沉默的,很明顯的,他無法理解自我的究竟實相(the absolute truth about the self)。
在本書的最後的一章提及不同時代所流行的不同的自我觀,最後成為統一的自我(unity-self)。布吒婆樓的三個觀點是:自我是身體,是心,或是無形的。他不了解所有的自我觀只是概念而已。同樣的,我們也有自己的見解,因為這些見解是「我的」,所以我們相信這些見解。想想看,這些見解是否有穩固的理論基礎?只因為「我」有對某人或某些事物的看法,這些看法是否真實不虛?當然,在絕對的層次,這些都是不實在的,因為一切事物都會變動、消失。即使在相對的層面也無法保證這些都是真實的。
我們應該經常檢視自己的想法,看看這些想法的來源。如果這些想法是負面的,就要知道這些想法的源頭,為甚麼會有這種觀念,其實所有的觀念都源自內心,我們所有的觀念都是心的投射(projection),甚至自我的觀念也是一種投射。當我們希望某個想法能實現時,是因為這種想法能滿足我們的貪慾。如果我們知道貪慾無法帶來喜悅,那麼我們會比布吒婆樓懂得更多,我們會觀察過去信以為真的觀念,所有的現象都不斷的在生滅,所以沒有永恆不變的「我」。
如果沒有我,那麼是誰指示身體去打坐,我們真的相信有個我在操控一切,就如演木偶戲的人操縱木偶一般。如果我們有這種觀念,就需要一再的探討這種觀念是否成立。
和布吒婆樓一樣,我們也受到不同的影響,我們被其他人的思想所影響,被我們的經驗和信念所影響。佛陀提供我們修行的方法,透過這些方法,我們可以略嘗解脫之味。沒有「自我」使我們能夠解脫,能夠去除貪與嗔。佛陀向我們宣說他所體驗到的、所證悟的法,我們只要依教奉行,便可究竟解脫。
第九章
出離、離欲和四聖諦
此時,布吒婆樓又開始一系列新的問題。我們都是這樣的,如果無法了解某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就會轉換話題。
世尊,「此想為人我耶?抑我與想為異耶?」甚難知之。如是世尊,復欲請問:世界常住耶?唯此真實而餘為虛妄耶?
佛陀回答道:
布吒婆樓,「世界常住(eternal)耶?唯此真實而餘為虛妄耶?」此為吾所不記。
佛陀和布吒婆樓接下來的問答如下:
世尊,世界非常住耶?
「世界非常住耶?」此為吾所不記。
復次世尊,世界有限耶?唯此真實而餘為虛妄耶?
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如是世尊,世界無限耶?唯此真實而餘為虛妄耶?
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這種現在看來非常麻煩的四段發問法,當時在印度非常流行:「是如此?非如此?既是如此亦非如此?既非如此亦非不如此?」布吒婆樓用這種問法問了十個被佛陀稱為「無記」(the Undeclared or Indeterminate Points)的問題。佛陀不回答,也不去討論這些問題。學者們認為:當時的苦行者、遊方僧和宗教領袖常用這些問題來表明各自的立場。佛陀和布吒婆樓的對話繼續:
復次世尊,此命與身為一耶?唯此真實而餘為虛妄耶?
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如是世尊,如來死後存在耶?唯此真實而餘為虛妄耶?
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如是世尊,如來死後亦存在亦不存在耶?唯此真實而餘為虛妄耶?
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如是世尊,如來死後亦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唯此真實而餘為虛妄耶?
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最後布吒婆樓問道:
世尊,凡此等等,世尊何故判為不記耶?
佛陀的回答非常有意思:
布吒婆樓,此不與義合,不與法(Dhamma)合,非梵行,非趣出離,非趣離慾,非趣止滅,非趣寂靜,非趣證悟,非趣正覺,非趣涅槃,是故吾判為不記。
這些問題對修行無益,對法無益,對滅苦也毫無幫助,不會使人出離、離欲、證悟和涅槃,所以佛陀把它們判為「無記」,不以討論。
對布吒婆樓來說,世界是否恆常對他的日常生活沒有影響;而靈魂與身體是否同一,又怎會影響他的幸福?至於佛陀死後是否存在和布吒婆樓有甚麼關係?這些問題無法使布吒婆樓解脫苦,所以佛陀拒絕作答。
在其他經典也有類似的討論。例如,有個叫婆蹉衢多(Vacchagotta)的外道曾問佛陀:如來死後是否存在?是否既不存在也非不存在?或既存在也不存在?佛陀說他不會討論這些問題。婆蹉衢多說他不了解,於是佛陀叫他去收集木柴,用木柴起火,接著叫他多丟一些木柴到火裡,並問他火勢變得如何。婆蹉衢多回答說:火勢很猛烈。之後佛陀叫他不要再丟樹技到火裡。一會兒,佛陀再問他火勢如何,他回答說火勢弱了,不久便熄滅了。佛陀告訴婆蹉衢多說:如來死後也一樣會熄滅,並問他:「火焰往前方、後方、左方還是右方?」婆蹉衢多回答說:「火焰並沒有往哪裡去,而是熄滅了。」佛陀堅持問他說:「火焰究竟往上還是往下?」婆蹉衢多回答說「火熄了,因為沒有燃料。」佛陀回答說:「如來也一樣,死後會熄滅,因為不再有欲望的燃料。」
今天,人們以不同的文字來問同樣的問題。即使在佛教國家內,對佛陀死後是否存在也有不同的看法。關於這個問題,佛陀說得很清楚:只要欲望之火不再有燃料,則身心都會止息。我們毋須再和別人辯論這個問題,或在心中和自己爭論。
佛陀告訴布吒婆樓,他不會回答一些對修行無益,對「法」無益的問題。在《箭喻經》中,佛陀以很好的比喻來說明這點。假設有個人被箭射中胸部,並在死亡邊緣掙扎,卻不讓醫生為他治療,堅持要先知道箭柄由何種木材製成,箭尖用的是何種毒素,箭尾的羽毛是鵝毛還是鷹毛,箭頭是甚麼東西做的,還有是誰射的箭,在哪個距離射的,為甚麼要射他?當然,等找到答案時,他已經死了。這個故事反映人們習於詢問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而不去修習可以解脫苦的方法。在經中,箭代表苦,佛陀是醫生,治療代表法(Dhamma),那個中箭的人是拒絕接受佛法的人,除非有人先把那些無關緊要的細節告訴他。
佛陀對布吒婆樓說一樣的話,佛陀說布吒婆樓的問題和修行無關,而布吒婆樓也只是問問罷了,他純粹是被佛陀所吸引,所以才花許多時間和佛陀討論。佛陀也認為布吒婆樓是孺子可教,否則不會花大半天和布吒婆樓討論。我們也非常幸運,如果沒有布吒婆樓的問題,佛陀就不會如此詳盡的解釋。
佛陀說:回答這些問題不會使人出離,離欲,不會使人寂滅、寂止、證悟和涅槃。「出離」是趨向開悟的重要一步,被稱為出世間的緣起,也就是覺察到自己的苦,並對佛法生起信心,同時也對自己能夠修行感到喜悅。接下來是禪修,也就是正定。禪修會帶來「如實知見」,也就是證得內觀智慧-知道一切事物都是無常、苦、沒有實體的智慧。「如實知見」可以使人出離世間,出離是解脫苦的第一步,在此之前,所有的修行只是準備而已。我們無法全心投入修行,是因為心仍然向外攀緣,認為只要找到意中人,找到合意的工作或理想的住所,就可以去除煩惱,認為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在這世間生活,為了生存,我們需要氧氣、陽光、雨水、食物和其他的東西;而內心的滿足是無法依靠外境的,我們不可能由外境獲得滿足,真正的滿足來自內心。要了解這個真理可能要花一段時間,有些人快些,有些人慢些,而有人永遠無法了解,這要視各人的業果和機會而定,當然,機會也就是業果(karmic resultants)。
出離並非指我們討厭這個世界、世人、大自然或其他事物。出離不等於厭惡,雖然有時出離被譯為厭惡。「厭惡」有負面的含意,而負面的心態會破壞修行。我們不是厭惡這個世間,而是不再執著外在的事物,不再認為這些事物能為身心帶來快樂,因此不會在世上追求絕對的滿足。年輕人很少能出離,當然也有例外。大部份的人都要在一再的失望後,才會以不同的方式來追求幸福。
禪修的人不一定能體驗到出離,因為許多人只是想為生活添加樂趣才來禪修。佛陀說這比不禪修要好。佛陀很樂意為人解答問題,在《布吒婆樓經》中,我們發現佛陀非常直接和簡明的回答布吒婆樓的問題:不要想外在的東西,想想如何出離。如果我們禪修的目的,是為了體驗生命中較高的層次,只要堅持不懈,總有一天會做到。
透過禪那,我們發現有不同層次的心識狀態,即使是凡夫俗子也能做到。此時,我們會發現這世間給我們的只是假的黃金而已,雖然閃閃發光,卻毫無價值。美麗的女子,英俊的男子,宜人的天氣,可口的食物,醉人的音樂,極佳的書本,這一切只是感官接觸而已,都是外在的,無法觸及內心深處。巴利文稱這些東西為誘惑(mara,魔羅)。我們不斷的被外境誘惑,並非因為外境多麼誘人,而是因為大部分的人認為幸福可以從外境獲得。有些人表面上看來事事如意,心想事成,我們會想:「為甚麼他們可以盡情享受人生,而我卻不能?或許照著他們所做的去做也會一樣快樂?」如果我們真的照著去做,就會失去追求解脫的機會。要做到出離,需要長期精進的修行,即使做到了,也只是踏出深入了解「法」的第一步而已。
出離之後是離欲,離欲是證入涅槃的起點。修行到了這個階段,出離心會非常強,一旦貪或嗔生起,我們會立刻去除貪與嗔,然而貪與嗔並非真的消失,只有在證悟前的最後一個階段(即三果阿那含),貪與嗔才會完全消失。即使如此,它們仍會若隱若現,但完全不會干擾我們;只有阿羅漢-開悟的人才完全沒有貪與嗔。離欲使我們不再執取、執著或是排斥反抗,雖然隨眠煩惱仍在內心深處,但我們能把它放下,因為我們了解出離的真理,只有如此,我們才會繼續我們的修行之旅。
出離和離欲是修行道上重要的階段,首先必須知道自己的苦。偶爾禪修是不可能出離和離欲的。知道自己的苦,並非指我們必須遭遇某種重大的悲劇。苦是心中的不安、焦慮和憂慮;有了苦,便無法安心。一旦體會到苦,對佛法的信心便會生起。這時我們才會認真修行,去驗證佛陀所說的法,而不是盲目的相信佛陀的話。投入修行會有法喜,這種喜悅遠超過世俗的感官之樂,而這種喜悅使禪修成為可能,這是出世間緣起的因果關係。下一步是安止定,接著是如實知見,也就是如實的了解一切現象都是無常、不圓滿(苦)和無我的。
經歷了一件事並不表示我們必定了解這經歷。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用很少的知識便可以過生活,正如閱報一樣,只需少量的詞彙就可以明白大概。我們的日常生活不需要高深的智慧,只要我們能夠處理日常事務即可;而遵循佛陀的教導,我們必須更深入,必須覺知當下所發生的事和每個念頭的生滅。
如果我們照著做,就會發現:無常是生活的一部份,這比起表面接受「一切都是無常的」或「吸呼是無常的」要深入得多,我們深深了解無常是與我們有關的真理。我們也以同樣的方法去體會苦,我們一再的體會到苦,知道內心深處的不安,知道自己花了多少時間去追求外在的事物。我們責備他人,認為自己的苦是他人造成的,忘了別人和自己一樣,內心也一樣不安,我們找一些理由來解釋內心的不安,這些表面的原因只解釋表面的經驗,無法說明內心深處的煩惱,因此無法根除苦。
覺知到無常和苦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在自己身上看到無常和苦,也要在每一件事物中看到無常。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每一棵樹,每一片葉子,每一根草都在宣說無常的真理。每天都充滿無常,我們可以從有數字顯示的時鐘上看到每一秒都在變動,無常就顯現在時鐘上,然而我們總是認為:雖然時鐘的數字在變動,而我們是靜止的,這怎麼可能?我們的身體和數字鐘一樣,每分每秒都在變化。
離欲對我們的生命有重大的影響,一切事物都有其因果,透過修行才能離欲。有時我們捨棄了某種欲望,我們以為已經離欲,所以當其他的欲望生起時,我們會感到訝異。當然能夠捨棄欲望是值得稱讚的,也非常重要,但不表示已經完全離慾,因為我們仍有欲望,所以仍要修行。在婆蹉衢多的故事中提到,當所有的燃料都耗盡時,火焰才會熄滅。有些人會說:「但我喜歡欲望。」如果我們如此認為,那麼只好等待,等到有所改變,或許是今生,或是來生,或是一百世以後,誰知道呢?或許是明天也說不定。對生命的態度改變,心才會改變,對事物的看法也會大不相同。
禪修得越好,心會變得越清明,越能看清生命的真相。大部份的人都生活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中,他們希望世界如同他們所想的一般,然而現實生活與想像並不相同,所以許多人不快樂。我們也不會安於現實,如果會的話,那麼所有的富人都會感到滿足,就不會有富人絕望的自殺。或許我們知道這些事,但我們有沒有對治的方法呢?我們所知道的和我們所做的有一大段距離。重要的是,如果真的知道要怎麼做,就要趕快去做,否則不會進步,因為知識無法帶來改變。
佛陀在《布吒婆樓經》中說道:離欲可以導致止滅、平靜和證悟。如果心中有貪與嗔,是無法超越自己的,因為心被貪、嗔所困。當我們的念頭不停打轉時,我們最能感受到這點。和布吒婆樓一樣,我們的心充滿各種想法和見解。只要心中有貪與嗔,我們就永遠無法平靜,也無法體驗到高超的意識境界。
在禪修時,如果心能平靜下來,就會了解這個世間只是為身體提供必要的東西,外在的事物無法帶給我們幸福快樂,所以不要太重視。當然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事,我們仍需注意,而在禪修時,我們應斷除貪與嗔,做到這點,才能達到更高的禪那和證悟。巴利文abhibba意指證智,也就是去除五蓋和隨眠煩惱,禪修到了這個境界,貪與嗔都會消失,不再障礙我們。
佛陀通常以四種方式回答問題:直接回答「是」或「不是」,有時會詳細解釋或反問,最後是以沉默作答。在《布吒婆樓經》中,佛陀對布吒婆樓說討論這些問題對修行無益。接著布吒婆樓問佛陀:作為導師的佛陀會討論那些問題:
如是世尊,世尊所記為何?
佛陀回答:
布吒婆樓,「此是苦」為吾所記,「此是苦因」為吾所記,「此是苦滅」為吾所記,「此是滅苦之道」為吾所記。
這是四聖諦,是佛法的精髓。布吒婆樓之前的問題太不切實際,佛陀把他拉回最基本的實相。四聖諦是佛陀證悟後所宣說的法,佛陀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證悟後,入定七天,出定後,他有系統的宣說四聖諦,幫助人類脫離困境。在開悟後,佛陀對以前的同修五比丘所開示的第一部經是《轉法輪經》,其中一位聽後立刻證果;之後,其他四位比丘也證果了。他們是第一批僧伽,是佛陀最初的弟子。
滅苦的方法是八正道,八正道可分為戒、定、慧三學,本書都提到了。布吒婆樓聽過有關持戒的必要,也聽過禪那即「定」的開示。當討論「自我」是否存在時,他已經初步接觸到「慧」。很明顯的,布吒婆樓到目前為止還認為「自我」是存在的,他將繼續問有關的問題,直到他成為佛弟子時,他才相信「無我」。
佛陀的教法永遠包含戒、定、慧三學,無論少了哪部份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值得遵循的修行法必定包括戒、定、慧三學。我們也把「定」稱為三摩地(samadhi),或譯為平靜、寧靜、寂止。平靜的心才能生起智慧。
布吒婆樓仍有問題:
世尊所記,為何故耶?
佛陀很有耐心的回答:
布吒婆樓,此合義合法,是根本梵行,趣向出離、離欲、止滅、寂靜、證悟、正覺、涅槃,故為吾所記。
此時此刻,布吒婆樓終於明白:
誠然世尊,誠然善逝。世尊請便,今正是時。
於是世尊起座而去。
布吒婆樓得到的啟示非常重要,只有問「對修行有益的問題」才有用。那時在印度或現在,那些婆羅門、僧侶、精神導師喜歡長篇大論的討論世界是否永恆,是否無限,靈魂與身體是否相同等問題。討論這些問題對修行無益,只會造成更多的空想,對修定沒有益處。
最有益於修行的問題是深入了解四聖諦,並在心中好好體驗。第一及第二聖諦是「苦」及「導致苦的原因」-也就是貪欲,執取與嗔心,我們幾乎時時刻刻都體驗得到。如果我們能了解這兩種聖諦,就能了解第三種聖諦:苦的止滅(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第四種聖諦:滅苦之道(道諦),也就是八正道可以導致解脫。問這些問題才有意義,我們必須深入探討,直到完全了解。我們自問:「我有苦嗎?如果有,是否把這些苦歸於外境?是否認為是外境或某人使我受苦?或認為苦是自己造成的?」我們必須一再的問自己:「是誰使我受苦?」在理智上,我們可以告訴自己:「沒有人有興趣使我受苦,沒有人會這麼做。」無論是如何合理的解說都沒有用處。我們必須了解苦是源於內心的貪欲、嗔恨和執著,一旦我們放下所有的欲望,苦會立刻消失。
有些欲望看起來是好的,例如,我們想有一節好的禪修,一旦我們這樣想,還能靜下來禪修嗎?當然不能!根本無法入定。如果有「我想要」的念頭,就會有苦;假如我們放下「我想要」的念頭,坐下來,盤起腿,把心安住在當下,沒有任何慾望,我們會發現真的很有效,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即使我們的心仍妄念不斷,只要放下欲望幾秒鐘,就會感到非常輕鬆。此時,我們放下重擔,就像放下沉重的包袱。當然,未受訓練的心會立刻重拾包袱,只要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放下,我們不但能熟練的放下貪欲,也能看到修行的成果:心量擴大、開闊、自在、輕安、平靜。
如果我們能全心投入禪修,又沒有任何期望的話,效果會更好。我們也會變得明智,知道要放下佛陀所說的純屬推測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修行沒有幫助。布吒婆樓很喜歡問這類問題,布吒婆樓所問的問題使我們了解甚麼是對修行有益的,甚麼是無益的。
第十章
貪愛的止息:趣向涅槃
在前一章,布吒婆樓對佛陀說:「誠然世尊。」而在佛陀離開辯論堂後,那些外道轉向布吒婆樓:
世尊去未久,苦行外道皆向布吒婆樓作譏誚言:「布吒婆樓,汝於沙門瞿曇(Gotama)所說,作如是讚嘆:誠然世尊,誠然善逝。然於世間常住耶,世界為無常耶,世界有限耶,世界無限耶,命與身為一耶,命與身各異耶,如來死後存在耶,如來死後不存在耶,如來死後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諸問,吾等不見沙門瞿曇確示一法。」
布吒婆樓聞是言已,告彼等苦行外道曰:「諸君,世間常住耶,乃至如來死後亦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諸問,吾固不見沙門瞿曇確示一法。然沙門瞿曇所說之道,如實真正,如法合法。
那時佛陀已經很有名了,外道們仍以「沙門瞿曇」來稱呼佛陀:而不是以覺者(Buddha)來稱呼,這意味著他們認為佛陀只是他們的一份子。另外,布吒婆樓用了「法」(Dhamma)這個字,現在我們用來指佛法(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那時,布吒婆樓不是佛陀的弟子,這是他第一次聽聞佛法,這表示當時常用「法」字來指絕對的真理、自然的法則。布吒婆樓繼續說道:
理智如吾者,何不讚嘆此善說法者耶?
雖然布吒婆樓不是佛陀的弟子,他發現佛陀的教法非常珍貴,合理。經文繼續:
後二三日,象首舍利弗與布吒婆樓詣世尊所,象首舍利弗禮敬世尊,坐於一面,布吒婆樓亦親禮世尊,慇勤問訊已,就一面坐。
我們假設象首舍利弗曾經聽過法,是佛陀的信徒,布吒婆樓只和佛陀互相問訊,然後告訴佛陀他離去後,那些外道嘲笑他的事。佛陀說:
布吒婆樓,彼等苦行外道皆悉盲目,為無眼子,唯汝一人,具眼士也。
佛陀經常用「眼中只有微塵」來形容那些容易了解佛法的人,事實上,佛陀在證悟後,坐在菩提樹下享受涅槃之樂時,並不想去教化眾生,因為他的教法與眾生所聽到的大不相同,所以眾生不會了解他證悟的法。最後,梵天(Brahma)向佛陀請法,請佛陀為了天人與人類的福祉,一定要弘揚佛法。然後,佛陀觀察眾生,發現那些「眼中只有微塵」的人,為了他們,佛陀決定成為他們的導師。佛陀繼續說:
布吒婆樓,我所說法,有決定記,不決定記。布吒婆樓,云何名為我所說法不決定記?
佛陀再度說明哪些是「無記」的問題,即:世界常住或不常住,世界有限或無限,命與身為一或各異,如來死後存在或不存在,如來死後亦存在亦非不存在等問題。
布吒婆樓,以此等不與義合,不與法合,非根本梵行,非趣出離,乃至非趣涅槃,是為不決定記(無記)。
佛陀再度強調,他只說趣向究竟解脫的法,所以無論佛陀教的是何種法,都指向同一個方向:究竟解脫。可惜無論是佛陀時代或者是現代,有許多導師都不了解這點。
今天,同樣的,修行的旅程引領我們一步一步趣向涅槃,而不是滅去(annihilation)。涅槃沒有這類東西,只有清明、圓滿和完全的覺知,以及無明的止息。這種覺知不是全知,佛陀說他無法同時知道所有的事,但只要佛陀去思考,就能知道任何事。雖然「全知」令人刮目相看,卻不是證入涅槃的目的,涅槃是無明的止息,苦的止息。
布吒婆樓,云何為我說法之決定記?亦即此是苦,此是苦因,此是苦滅,此是滅苦的方法。…以此等與義合,與法合,是根本梵行,是趣出離,離欲,止息,平靜,證悟和涅槃,是故此等為我說法之決定記。
佛陀把布吒婆樓帶回四聖諦,向他說明如何一步一步的修習內觀,趣向涅槃,直到所有的無明消失。
我們已經知道出離和離欲了,接下來是止息(cessation)。止息指想、受的止息,指在九禪進入滅盡定或滅受想定。止息也指苦的止息,如佛陀所說的,止息指三種貪愛不再生起。這三種貪愛是:「欲愛」,指渴求感官欲望的滿足;「有愛」,指渴望生命的存在;以及「無有愛」,指渴望生命不存在。這三種貪愛是我們生死輪迴的主要原因。我們或許會責怪父母,讓我們學了許多壞習慣和給我們許多壞的影響,父母親可能會做出許多沒有智慧的事,因為他們尚未開悟,我們不應該責怪父母,是我們的貪愛把我們帶到這個世界,來到特定的家庭,所以我們應該觀察自己的貪愛。
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渴望感官慾望滿足的「欲愛」,如果我們能自我觀察,可以看到心中的「欲愛」。而渴望生存的「有愛」就深入得多,「有愛」是我們最強烈的欲望,是使我們生死輪迴的主因。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難覺察到「有愛」。人們經常使自己忙得團團轉,去避開看到不如意的事,這是人們對治苦的方法。如果我們深入觀察「有愛」,就會了解佛陀的教導,因為渴望生命存在的「有愛」會導致持續的苦。
「有愛」使我們去找些東西來填滿自己的心,這是為甚麼我們會不停的想,不斷的動,以及去避開不如意的事。想想看我們早上的床是甚麼樣子,亂成一團,為甚麼?因為即使在睡覺,心仍不得安寧,仍有苦受,所以身體會動來動去。我們醒來的第一個念頭是甚麼?我們會不會想:「啊!活著真好!」會這樣想的人非常少。大部份人會想:「又來了!」或是類似的話。有多少人能覺知醒來時的念頭?意識是如何生起的?念頭是如何生起的?我們如何造成這一切?我們告訴自己,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很無聊。其實這些只是在支持一種假象:自我。這個自我很忙碌,因為忙碌表示自我很重要。這個假象滿足了「有愛」,事實上,我們所有的活動都朝向這個目標-有愛。如果我們仔細觀察自己,我們會發現果然如此,即使是動機最善良的行為都是為了滿足有愛。
仔細審視一天的生活對修行很有幫助。審視今天的生活,由於時間太近,可能有點難。我們可以想想昨天是如何過的,做了甚麼事?想些甚麼?如何保持自我這假象?我能夠觀察到不斷生滅的身心現象中的「有愛」嗎?身心不斷的變動,我們的心想東想西,想將來可以做些甚麼,想過去做了甚麼。只有當我們不斷的想,才知道自己的存在。所有的心理活動只為一個目的:滿足「有愛」。
禪修時,只有一個禪修對象-如觀呼吸,就可以使我們去除妄想。禪修時,如果我們能去除妄想;禪修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可以去除妄想;去除妄想後,心就會平靜、寧靜。
「無有愛」(the craving for non-existence)只是硬幣的另一面,源於同一種假象-即有「我」的存在。不過此處的「我」並不想存在,可能是生活中有些事情非常糟,使「我」想逃之夭夭,也就是渴望不存在。「有愛」因為渴望存在,所以會障礙我們體證涅槃。如果我們了解苦,也願意審視「有愛」,那麼要小心不要墮入「無有愛」的陷阱,如果我們覺得人生充滿苦,因此想逃避,這也是一種貪愛,因為是我想要「去除」某種事物,這是行不通的。我們應該放下所有造成「自我」假象的事物,要一再的、如實的觀察身心的變化,而不是如我們所想的一般。假如我們有太多的成見,就不會進步,就像嘲笑布吒婆樓的外道一樣,他們不想聽任何新的理論。布吒婆樓則不然,但到目前為止,他仍不得要領。
觀察這三種貪愛非常重要的,要深入觀察,任何時候都可以觀察,在禪修時、坐在樹下或走路時都可以。
接下來佛陀要說的是平靜,我們要學習去除妄念,這些妄想使心無法平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無必要的思考,我們有念頭,是因為要讓心忙碌,要觀察這點並不難,我們可以用修行來去除妄念,此時只有覺知,心是清淨的,好像透明一般,心是平靜的,這種內心的平靜有助於恢復精力。我們的念頭使我們疲累,我們的工作或許只需少量的體力,或許只是按按鍵盤或揮動筆桿,但一天下來卻疲憊不堪,這是因為心不斷的思考、盤算和反應。當沒有必要時,我們是可以不去想的。
要做到以上所說的並不容易。只有當「有愛」止息,純然的覺知才會生起。在止息貪愛之前,我們必須了解它的含意,我們必須觀察貪愛不斷生起,以及永遠無法滿足,貪愛會使我們不安和焦慮,這些在外表是看不到的。我們的內心經常不安,我們使這種不安合理化,並歸罪於外在因素,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有愛」。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的確是這樣,那麼我們就會有恍然大悟的經驗。禪修進入狀況時,會有平靜的心,而平靜的心比較客觀,也更容易觀察到心中的貪愛。通常我們會告訴自己:「這就是我,我有許多事情要做,雖然會花許多時間,但如果我不去做,誰會去做呢?」有許多類似的念頭會生起。
如果只觀察一個人的行為和表現,我們會發現都是內心在推動的,這些都是「有愛」的表現;那麼修行的動力是不是呢?這是一種矛盾,我們需要修行的動力,去觀察和了解佛法也需要動力,而為了證入涅槃又要將這動力放下。從需要動力和放下動力,就好像轉換軌道一樣。當我們深入觀察自己時,我們會知道心中所有的念頭,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我們毋須厭惡、責備或怨恨自己,也不會有罪惡感,心中所有的念頭都是人性的一部份,首先我們要知道它生起的原因,然後超越它。觀察「有愛」是非常有趣的修行,雖然有點難,但能帶來重大的成果;而容易做的事,通常不會有大的成就。
心止息和平靜後,佛陀提到下一個階段:證悟。證悟有不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指我們知道已經去除五蓋以及和五蓋有關的隨眠煩惱。只有斷除有愛才能去除五蓋。在清淨道上修行,我們不斷的減輕五蓋的影響;而支持我們修行下去的就是禪修、正念。此時,我們仍不能根除五蓋,因為仍有貪愛和嗔心,直到修行的最後階段才能徹底斷除貪與嗔。隨著證悟而來的是涅槃,涅槃是修行之旅的終點。
透過禪修和淨化內心可以體證涅槃。觀察內心深處的貪愛-貪求生命的存在,可以知道貪愛是使我們去做最愚蠢和可怕的事的關鍵,使我們從早到晚去做那些我們經常做的事。
現在,佛陀再度向布吒婆樓講述內觀智慧之道,這條道路通往涅槃和四聖諦。佛陀知道布吒婆樓仍無法領會,所以佛陀用其他的詞句來說明:
布吒婆樓,或有一類沙門婆羅門謂:「我於死後,一向安樂,亦且無病。」
這是熟悉的天堂的觀念,有天人在彈奏豎琴和永遠幸福快樂的地方。現在,在某些佛教圈子仍非常流行這種觀念,例如,藉著唸誦佛陀的名號,希望能往生淨土,永享快樂。
我訪彼等,如是問曰:「諸友,汝等謂我於死後,一向安樂,亦且無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見,真實否耶?」彼等聞是言,報我曰:「然」。
我又問曰:「諸友,一向安樂之世界,汝等實知實見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否也。」
我又問曰:「諸友,汝於一夜或一日,於半夜或半日,亦曾審知有一向安樂之我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否也。」
佛陀不但告訴布吒婆樓那些婆羅門所宣揚的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理論,而且指出如果想在這個世間找到快樂,等於走上歧路。很明顯的佛陀要布吒婆樓去思考這個問題,我也建議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們拿這一天來反省,用剛才觀察「有愛」的方法,觀察我們如何周旋在不同的事情中?我們做了一件事後,由於不滿意,又去做另一件事,正如佛陀所說的:「你們曾於一夜或一日中,感到完全快樂嗎?」
這並非指我們必定不快樂,雖然有時我們的確不快樂。如果我們回想平常的日子,會發現甚麼?發現對生活不會十分滿意,或許有片刻的歡樂,但能持續多久?而那些情緒和念頭無法帶來平靜或涅槃;這些情緒和念頭又不斷生起,這就是苦,這種苦是因為得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或是無法擺脫我們不想要的事物。我們應該盡可能仔細觀察這種苦。
我們並非對生命厭倦,如果我們正確的觀察,反而更容易接受生命中不圓滿的現象,既然佛陀已經找到解決方法,我們便應跟隨他的腳步,親自去驗證佛陀所說的法。去觀察心中的不滿可以減輕苦,因為我們可以接受生命本來就是如此。而一般人對苦的反應是感到痛苦和哀傷,這是無濟於事的,當我們受苦時,我們無法如實觀察事物。所以觀察「這一整天,心起了甚麼念頭」是很有幫助的。生存是為了甚麼?
佛陀接著問那些婆羅門和苦行者:
「諸友,趨於一向安樂世界,惟此道可實現,惟此路得通達,汝等曾了知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否也。」
今天,我們可以在許多敘述神秘經驗的雜誌上找到這些理論和觀念-宣稱能獲得安樂的方法,很明顯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只要仍有「有愛」,一定還有苦。尤其是在「有愛」的背後隱藏著對不存在或斷滅的恐懼,顯現在對死亡的恐懼。或者有人會說:「我不怕死。」因為他們認為死亡是很容易面對的,他們會說:「只要不受苦就好。」或「只要比我心愛的人先死就好了。」而對死亡的恐懼是非常真實的苦,隱藏在「有愛」中。
當我們覺得被忽視,不被接受或沒有人愛時,也會有斷滅的恐懼。為了得到別人的欣賞,有些人會用盡一切方法,這樣的生命非常不圓滿,因為要仰賴別人的意見和情緒,這是非常不可靠的。
當我們認為自己很特別和與眾不同時,就需要一些東西來支持;當我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時,就需要從別人那裡得到。雖然有時我們會得到我們渴望的愛與讚賞,而長遠來說是行不通的,因為沒有人可以永遠得到讚賞。因為自我是建立在假象(illusion)上的,需要不斷的支持。自我的假象越深重,所生起的貪愛就越危險。正如一個很肥胖的人想走過一道很窄的門一樣,一定會撞到門的兩側。
同樣的,如果我們去保護「自我」,那麼即使是些微的批評或不諒解也能傷害「自我」。自我越大,越容易受傷,反之則越小。如果沒有自我,就根本不會受傷。如何縮小自我?去觀察,每分每秒的觀察我們的「有愛」,內觀智慧就會增長。
所有的人都感受到苦,卻不知道如何離苦,我們以為修行是唯一可以減輕苦的方法,我們透過去做,去說,去體驗某些事,希望能帶來快樂。佛陀離苦的方法不是這樣,佛陀說如果要真的快樂,唯一的方法是去除「自我」這個假象,亦即完全去除「有愛」。佛陀繼續說:
我又問曰:「諸友,生彼一向安樂世界之天神曰:『尊主,若欲實現一向安樂世界,當行善業,當步正道,所以者何?吾等所行正爾,故得生於一向安樂世界?』汝等曾聞其說示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否也。」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彼等沙門婆羅門所說,合正理否?
對於一些錯誤的觀念,佛陀會指出這種觀念是愚痴的,佛陀不認同一些無法探討問題核心的修行指導,《布吒婆樓經》不是唯一記載佛陀批評外道的理論是愚痴的,特別是當他們誤導他人時。此時,佛陀舉了一個比喻:
譬如有人作如是言:「吾於此國中求交且愛第一美女。」餘人若問曰:「吾友,汝於此國中,求交且愛第一美女,則汝當知,國中所謂第一美女,屬剎帝利族耶?婆羅門族耶?吠舍族耶?抑首陀羅族耶?」彼聞是言,答曰:「不知。」
又問彼曰:「吾友,汝於國中求交且愛第一美女,名何姓何?彼女身軀長耶短耶,抑適中耶?彼女皮膚靑黑耶?黃金色耶?彼女所住,為村落鄉鎮抑城市耶?」彼聞是問,答曰:「不知。」
又問彼曰:「吾友,汝所求交且愛者,汝不知其人,不見其人耶?」彼聞是問,答曰:「唯然。」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此人所說合正理否?
布吒婆樓回答:
世尊,此人所說,實不合正理也。
布吒婆樓似乎對佛陀更有信心,因為現在他稱佛陀為「世尊」。佛陀繼續說道:
布吒婆樓,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謂:「我於死後一向安樂,亦且無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見。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彼等沙門婆羅門所說,合正理否?
世尊,彼等沙門婆羅門所說,實不合正理也。
佛陀想讓布吒婆樓知道,這些導師並沒有任何證據來支持他們的信仰,他們非常愚痴,就像想找國內最美的女子的人一樣愚痴,因為他不知道最美的女子是誰,住在那裏。
許多宗教都相信有一個永遠快樂的世界,如果我們過著正當的生活,沒有犯許多罪,死後這個「自我」就會永遠幸福。佛陀從來不認同這種理論;相反的,佛陀說:通往快樂的唯一道路是觀察「自我」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是心想出來的(mental formation)。佛陀舉了另一個譬喻:
例如有人,於四衢道處,欲樹立一梯,以登殿堂。有人問彼曰:「今者,吾友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在東方,西方,北方,抑南方耶?此殿堂高耶低耶,抑適中耶?君知之乎?」彼於此問,答曰:「不知。」
此人又問:「吾友,汝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君不知亦不見耶?」彼於此問,答曰:「唯然。」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此人所說合正理否?
世尊,此人所說實不合正理也。
換句話說,有人想去夢想中的快樂天堂,卻不知在哪裏,或是如何去。佛陀花了不少時間來說明這點,佛陀想指出布吒婆樓的錯誤觀念,尤其是有關自我的理論,只是這次佛陀以不同的主題來說明,佛陀對布吒婆樓有無限的耐心,以不同的方法來解說「法」,希望布吒婆樓能夠了解。我們可以把自己當成是布吒婆樓,因為要了解「自我」為何物並不容易。這個「自我」坐在這裡,想得到快樂,卻不知道「自我」本身會妨礙快樂,妨礙知足和滿意(fulfillment)。
如果我們主觀的看自己,可能會看到「自我」,如果我們客觀的觀察,就會發現「自我」只是一種觀念,是心理作用而已。禪修的人都知道,根深蒂固的觀念是很難改變的,但至少我們知道該如何處理。我們知道是甚麼引起內心的憂喜煩躁與不安。為甚麼我們不斷的渴求和排斥某些事物,這是渴望生存的「自我」假象所造成的。當我們越了解實相,就越能感到佛陀的偉大,因為在人類歷史上,佛陀首次將人類的處境和超越的意識,如此明確的勾劃出來。
許多人皈依佛陀,向佛陀祈禱,卻不知佛陀偉大之處。如果在今生今世能了解佛陀的偉大之處,表示我們有相當好的業果,這是我們應該把握的。去了解佛法,去探討生命的本質,指我們能夠在我們身上發現實相、真理,我們往內心觀察,如果我們觀察自己的心就能了知法,這並非指我們要去除「自我」,而是要了解自我只是一種假象,如果不了解,就永遠放不下。深入了解法,了解生命的實相,是放下的先決條件。
第十一章:滅除自我的假象
以前布吒婆樓在界定「自我」時碰到很大的困難:
布吒婆樓,有三種我得(acquired self),即粗我得(gross self),意所成我得(mind-made self),無形我得(formless self)。
我們會誤解acquired這個字。如果用另一個字assumed(假設的),自我就會更清楚,指這個「自我」是假設的。
何者是粗我得?粗我得有形,由四大所成,段食所養者,粗我得也。
很明顯的這是指身體。身體和欲界(kama-loka)有關,Kama是欲望,loka是地方或處所的意思。欲界是我們所住的地方,我們有種種的欲望,欲望是我們的一部份,也給我們帶來許多麻煩。要超越慾望必須很努力,要知道慾望所帶來的苦,雖然我們仍在相同的世界裡,最後我們仍可以達到沒有欲望的境界。
和布吒婆樓一樣,我們以為「粗我得」是自己。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有很矛盾的感情:當身體疼痛、生病或不聽話,我們就會很討厭;當身體健康,有許多快樂的感官接觸,我們會覺得「有」身體是相當不錯的。我們不認為身體就是我,而認為我們擁有身體,把自己當成某個人,也就是把身體當成自己,沒有發現身體也是一種自我的假象。
佛陀告訴我們:身體的欲求是永遠無法滿足的。佛陀說:身體有各種感官慾望,我們應該觀察這個身體,觀察「身體」是我們所要面對的對象,而不是我們所擁有的,因為「擁有身體」的觀念與事實不符。沒有人想讓身體生病,受傷,老化和長得醜,沒有人要讓身體死去,可是身體卻有這些事,如果我們真的擁有身體,為什麼身體會這樣?
身體由四種元素構成,即地、水、火、風。這四大種又稱為色(materiality,物質),由食物所養。身體有許多慾望,如果沒有慾望,生活會簡單多了,我們不需要廁所、浴室、淋浴,也不需要廚房;我們不需要花這麼多的時間、精力去買東西,去種植蔬果,去準備食物來養活這個身體。
讓我們想想看我們家裏有哪些東西?一切都為身體而設:廚房、浴室、臥室、起居室,還有舒服的椅子、躺椅。如果住在高樓,可能會有電梯,「身體」可以很輕易的到達住處,這些設備都是為了身體,怪不得我們會視身體為自己,或認為身體屬於我的?
我們對身體也有許多要求,希望身體不要太胖,太瘦;不要太高或太矮;不要有任何的疤痕或傷口,不要有缺陷(blemish)或骨折。即使是最輕微的苦,也不應該有,可惜身體總是不聽話,而自認為擁有「身體」的人,對它一點辦法也沒有。
有關「擁有權」的問題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尤其在禪修結束時,當心比較平靜和清明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假設「我就是這個人」,而不會說:「我就是這個身體。」總會把自己想成是某人。我們需要客觀的去觀察身體的擁有者,要找身體很容易,看看它、摸摸它就行了,但誰擁有它呢?我們可以說擁有者是「我」。然而「我」又是甚麼呢?在哪裡?在哪裏可以找到?當我們深入探討這些問題,就知道不可能找到合理的答案,這是佛陀稍後會為布吒婆樓解釋的。
告訴他人:「我是這個人」是一種謬誤,是很難說服他人的。照鏡子時,我們看到鏡中的「我」,我們非常關心這個「我」,雖然我們的視力非常有限,只能看到外表,無法看到內心深處,可是我們仍深深相信「我」就是這個身體,並花許多時間來使身體更美好,這是認同身體就是我。要看出這種謬誤,必須有平靜的心和內觀智慧。平靜的心與內觀智慧,會以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事物。
接著,佛陀向布吒婆樓解釋「意所成我得」:
何者是意所成我得?意所成我得有形,肢節具足,諸根圓滿者,意所成我得也。
在思考的過程中,常會有觀察者和其他心理活動的存在。當我們認同(identify)觀察者與我們的念頭、反應、感受或其他的感官接觸是「自我」時,這個自我就是「意所成我得」:把心、意當成自我。當我們修行一段時間後,我們會把「觀察者、覺知者」視為自我。我們應該儘量深入觀察,去找出這個覺知者,最後會發現並沒有「人」存在,而我們假設它存在,所以佛陀才稱之為我「得」(an “acquired” self)。
這種說法很先進,指出存在的真相,卻不容易掌握,因為和一般人所相信的理論不同,所以我們必須觀察這些信念所帶來的苦。當我們發現苦就在心中,而不是「那些可憐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苦就在我們內心,當我們知道苦及其原因,就能看到真相。如果我們所相信的理念,以及所做的事是為了「自我」,那麼必然有欲望。當我們了解這點,就略為了解佛陀的教導。
佛陀也認為這種說法很難令人接受。通常我們以180度相反的觀點來看每件事物,很自然的,我們的問題來自相反的觀點。所以當談到究竟實相(absolute truth)時-即佛陀此處所說的法,我們不能以相對層次的問題來問。相對層次和絕對層次就像兩條鐵軌,永遠平行,沒有交集。例如,有人問:「如果沒有自我,那麼在靜坐的是誰?」以相對層次而言,是「我」在打坐;以絕對層次而言,則「無我」。
當然,佛陀兩個層次的法都教,當他教導正念、守護根門、正知或持戒時,是在相對層次說法,所以有個「我」在修行。我們必須仔細分辨這兩個層次的法,當佛陀提到「我」時,不是「粗我」就是「意所成我」,我們不可以用日常的二元化的角度去理解。
我們必須接受佛陀所說的絕對層次的法,並以此來觀察身心活動,以獲得內觀智慧;或是置之一旁,直到修行功夫深厚和禪定日深,可以修觀為止。真正的選擇只有這兩個,第三個選擇是加以否定,但這會有反效果,使我們在原地踏步,並深信有「自我」。後者是不理想的觀點,因為我們經常要劃分界線,將「自我」劃在一邊,而這世間是另一邊。「自我」不只是旁觀者、觀察者,而且經常是有敵意的,因為外在世界不能滿足自我的需求。
由於人人都以自我為中心,所以當我們要面對二元世界時,有時會害怕,因為一個小人物要面對二元世界,會有無助感,該如何面對呢?有些人到了受不了時,會放棄面對;而大部分的人是轉移目標,讓自己忙得不可開交,就沒有時間去想這個問題,這只是權宜之計,無法避免老、病、死,也無法對治我們的愚痴和不適當的反應,當然也無法去除苦。所以佛陀一再的說明「四聖諦」,除非我們了解第一聖諦:苦諦,否則根本無法入道。
我們對世間的反應只會帶來更多的苦。我們相信在皮膚底下有一個自我,無論我們如何保護和珍惜,卻往往無法如願。在四個色界禪那也有「意所成我」只是此處的「意所成我」是純粹的觀察者,在四禪時,「意所成我」變得非常隱微,幾乎不能覺察到。
在日常生活中,這個由意念所成的「自我」幾乎無所不在,使人完全相信它的存在,因為我們一直感到它的存在,並一再的以它來活動,所以從不懷疑這個自我;直到我們遇上佛陀深湛的法。佛陀在此經中所說的法,大部份和相對層次有關,教我們如何把負面的念頭改為正面的。此經在此處理佛法中最高深的部份。
此書所提到的,在其他宗教也有類似的說法,只是大部分沒有詳細的指導。從古至今,不同的神祕學家都試著表達此一層次的經驗,但往往被自己的宗教信仰所限制,所以難以窺知。另外,這類經驗往往由頓悟而來,很難以文字形容,所以大部分的人不理會(ignore)這些經驗,然而中古時代基督宗教神祕主義者、回教蘇菲派(Sufi)和印度教大師的智慧語錄,有關禪那經驗的記載相當豐富。有些學者會加以研究,而對大部份的人而言,這個主題是毫無意義的,也沒有興趣,因此他們向外尋求,而非向內,希望能找到止息苦的方法。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為了想脫離苦,否則會苦惱不斷,這似乎很有道理。然而我們忘了我們的動機,我們有各種的觀念和藉口,如:「責任,事情總要有人做,可以增加知識,可以使自己快樂」等等。如果我們能了解我們的動機是為了解脫「苦」,那麼,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會有內觀智慧。所以佛陀證悟的宣言都是與苦有關的,或許有人認為這是負面的,而佛陀只是把事實說出來,並說明超越苦的方法。
佛陀繼續說:
何者是無形我得耶?無形之想所成者,無形我得也。
「無形我得」只能從無色界禪那中體驗,因為「無形我得」既沒有身體,也沒有心識狀態。在空無邊處及識無邊處沒有任何邊界,此時,只有想(perception)。如果沒有「想」,我們將無法知道我們所體驗到的「空無邊處」及「識無邊處」,因此,我們假設自我是「想」。
想、覺知和意識,是我們最後的憑藉,如果放下「以身體為自我,以心為自我,以念頭思想為自我,以感受為自我,以觀察者為自我」的觀念的話,只剩下意識,所以說「我」就是意識。
我們仍活在相對的、二元的層次中,只是不常發生。有「我的」想,這是與「你的」想相對的。或許「你」所進入的六禪有特殊的「想」,而「我」沒有。所以「我的想」與你的不同,這也是二元的觀念。這有兩種不好的結果:一是優越感(我的境界比你高),二是自卑感(我不如你),兩者都是不對的。
意識或想,沒有其他的含意,這兩個詞我們都可以用,雖然「想」和「標明」有關,如我們在前文討論「守護根門」時所說的,但此處所強調的是純粹的覺知。
有個故事很貼切的說明不是二元的「想」。有位長老帶幾位年輕比丘到森林裡散步,突然一群強盜把他們圍住。強盜要求那位長老選一個人出來當人質,以便寺院交錢贖人。他們再一次問長老,但長老仍保持沉默。他們第三次問長老,長老仍然沒有回答。這個時候,他們生氣了,說道:「你怎麼不答我們的問題?有什麼問題?」長老回答說:「如果我指其中一位年輕比丘留下,那麼他就是比較低下的;如果我讓自己留下,那麼我就變成比較低下的,而我和年輕比丘們事實上沒有分別,所以不知道應該指哪個給你。」那群強盜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便放了他們。
只要我們認為自我是存在的,無論是個體或個人的身份(identity)都是有限的,都非常依賴感官接觸,因此,苦永遠無法止息。佛陀接著說:
布吒婆樓,我之說法,實為欲使永斷粗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污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自身證悟,至於安樂。
接著佛陀用同樣的話來說明如何斷除「意所成我得」及「無形我得」。有些人把「斷除粗我得」視為斷滅,這是誤解。在某些經典,佛陀說得更清楚:「我所說的法,是要斷除粗我得的假象」。我們不是要斷除生命或一些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是要去除「自我」的假象。
在日常生活中,為甚麼我們不能去除「自我」的假象?首先,我們必須看看有沒有這個必要,也就是我們是否知道自己的苦。其次,要知道如何對治這些苦。我們不能只說:「好吧,我不再相信有自我。」這是無法解脫苦的。我們必須體驗到無我,至少一次,看看沒有這個「自我的假象」是何等光景,我們必須禪修才可以做到。
這是佛陀教導禪那的原因,透過修習禪定和內觀智慧,我們可以觀察苦;我們可以體驗片刻絕對的寂止,此時沒有「想」,沒有自我投射(self-projection)只有解脫、自在、歡喜的感覺,以及對能證入實相的感恩心。要有這種境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我們必須入定,心必須專注一境,不動搖,不散亂;其次,我們對自己能覺悟要有信心,一旦體驗到安止定,我們會知道這是我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佛陀所說的法,我們可以用來去除「自我」的假象,以便「斷離染污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自身證悟,住於安樂。」除了智慧以外,我們也可以用觀智(insight)一詞,兩者互通,或說是「內觀智慧」。透過高超的智(super-knowkedge)所證得的智慧很重要,這種智無法從儀式、上師或信仰獲得,只能從修行中獲得。「高超的智」非普通的智,它與我們的經驗有關,對「自我」的意義沒有任何疑惑,做個過來人有「了解的體驗」。佛陀自稱為「指路人」,所有的導師只能指路,走不走就靠我們自己。
在佛陀時代,有許多人第一次聽佛陀說法就開悟了,這是佛陀特有的智慧,能啟發信眾。在東方,人們比較有宗教熱誠,西方人這方面就比較難做到。雖然我們無法聽陀佛說法,但可以閱讀佛陀留下來的許多開示和修行上的指導,我們只要跟隨他的道跡就行了。
我們透過高超的智「證悟和獲得」智慧。「證悟」指有所體驗;「獲得」指我們對它有深入的了解。接著,佛陀說:「斷離染污法」,一旦「自我」的假象消失,我們的心就不會再有負面情緒,我們一再的觀察心,就可以得知這善果有多大,這叫做「審察智」(reviewing knowledge)。
佛陀說:代替「斷離染污法」的是「增長清淨法」,所有的貪與嗔都來自「自我」的假象,一旦自我的假象消失,內心剩下的只有純潔和明淨。
「自我」需要保護,需要感官的滿足,也需要安全,然而這個世間哪裏有真正的安全?我們買不到,卻讓保險公司賺了一大筆,而內心深處仍缺乏安全感,是誰在感受?當然是「自我」了。然而,如果沒有「自我」,就沒有「人」需要安全感了。
身和心只是身心而已,自我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們對這種說法強烈抗拒的話,這表示我們對自我的執著是多麼強。我們要做的是多體會苦,當我們感受到苦時,會問:「為甚麼會有這些苦?一定是某人或某事使我受苦。」直到有一天,我們會知道:其實,苦在心中。
遵循佛陀的教導,也就是依法修行。當我們修行日久,事情會改變,「清淨法」會增長。內心會淨化,不論是理智的心(mind)或情感的心(heart),由「以善心代替惡心」開始,也就是以正面的心態來代替負面的心理反應,例如,「厭惡、嗔恨、抗拒、反抗」,無論我們認為這些負面情緒的生起是多麼的有理由,這些負面情緒也會帶來許多不快,所以只有愚昧的人才會執著它們。一旦我們學會「以善心代替惡心」,而且能運用自如,我們便可以去除負面的情緒,讓快樂的心境生起。
在這個世間,在任何城市,當我們走在街上並觀察人們的臉,會發現很難找到一張快樂的臉,快樂遠離人們,因為人們的心中充滿貪欲。佛陀說:只要能放下「自我」,會使「染污法消失」,那麼「清淨法就會增長」。我們發現所有不愉快的心境都和「自我」有關。通常我們認為所有負面的情緒都由外境引發,例如,有人做了令人不愉快的事,即使不是針對自己,我們也會生氣和不快,這就是「染污法」。這種情緒反應會帶來傷害,而且毫無用處。碰到這種情況,我們有更好的處理方式,我們真的沒有理由去為「自我」找藉口;如果有,那只是「自我」在作祟罷了。佛陀繼續說:
布吒婆樓,汝意或謂:「斷除染污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欲自證悟,至於安住,然而(有情)猶住苦中。」布吒婆樓,勿作是念,所以者何?若斷除染污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能自證悟,而自安住,是則愉悅歡喜,成就輕安,又得正念正知,住於安樂。
布吒婆樓還沒有開始修行,所以不知道「斷除染污法」是什麼滋味,佛陀把布吒婆樓可能會想到的問題先說了,佛陀告訴他:如果認為此時會不快樂是錯的。佛陀說:快樂不是指喜悅興奮的心境。當我們有了正知正念和平靜所生起的捨心(equanimity),這種捨心會帶來平靜之樂。
千萬不要混淆「捨心」和「冷漠」,一般人很容易混淆。冷漠指我們不去面對所發生的事,「捨心」指以正念正知和平靜的心來面對所發生的事。
對禪修的目標(所緣境)保持覺知,可以培養正念,在日常生活中應盡可能保持正念,無論做什麼都要保持正念。當心沒有任何雜染,正念正知就會現前。其實正知(clear awareness)是內觀智慧的別稱。「正知」不只向內觀察自己,同時也使我們以悲心而不是以責怪及厭惡的心,來觀察他人及其行為。
當心清明時,只會認知、觀察,不會抗拒。這裏提到的平靜是捨心的一部份。我們在禪修時修習捨心,並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漸漸的捨心就成為我們的心境。
接著,佛陀繼續說明去除「粗我得」的方法;也以同樣的方法來去除「意所成我得」和「無形我得」。佛陀說:
布吒婆樓,若有人向我問曰:「尊者,汝之說法,云何永斷粗我得?依之隨入,斷除染污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耶?」於如是問,我當答曰:「吾友,我之說法如是,欲使永斷粗我得,依之隨入,斷除染污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
此處的「粗我得」指「這個人是」,指我們自己。佛陀又提到「意所成我得」及「無形我得」。換句話說,這三種「自我」都是假象,無論在身、心或意識中都沒有「我」,在我們身上也找不到一個「擁有者」,所以不能說「我是擁有者」;在這三種自我中,也找不到觀察者,所以不能說「我是覺知者」,因為這只是心的作用-行蘊(mental formation)罷了。接著,佛陀問布吒婆樓: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我之所說,合正理否?
世尊所說,實合正理也。
佛陀解釋說:
布吒婆樓,猶如樹立一梯於殿堂下,欲登一殿堂,旁人問彼曰:「今者,吾友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在東方耶?在西方耶?在南方耶?抑北方耶?高耶低耶?抑適中耶?君知之乎?」彼答問言:「我欲立梯於殿堂下,為欲如是而登殿堂。」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此人所說合正理否?
世尊,彼之所說,實合正理也。
布吒婆樓,此亦如是,設若有人,向我問言:「尊者,汝之說法,云何永斷粗我得?云何永斷意所成我得?云何永斷無形我得?…依之隨入,斷除染污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自身證悟,至安住耶?」
於如是問,我當答曰:「吾友,我之說法,如是永斷是粗我得,…永斷意所成我得,…永斷無形我得。依之隨入,斷除染污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自身證悟,如是乃至住於安樂。」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我之所說,合正理否?
世尊所說,實合正理也。
佛陀尚未叫布吒婆樓去修習,只是讓他去思考是否合理,而布吒婆樓表示這種說法合理。
當我們能放下這些假設的自我,「染汙法」就會消失,而能於當下「清淨和智慧充廣」,這點很重要,我們不只能獲得智慧,還能安住其中。內觀智慧是不會退失的,而平靜和輕安的禪那境界很容易退失-如果我們不禪修的話
。當我們獲得內觀智慧,整個人的態度、威儀和內心的感受都會改變。如果我們真的沉入內觀,內觀智慧便永遠不會退失。所以在修習安止定後,我們會自問:「我剛剛學到了甚麼?從禪修中獲得哪種內觀智慧?」
佛陀所教導布吒婆樓的法,還未能改變他,布吒婆樓必須先對法生起信心,才會開始修習。而改變前需要先對修行有所體驗,即是所謂的「了解的體驗」(understood experience)。在心已經平靜到某種程度時,我們應該自我審察:「我的苦如何形成?苦生起時,我能覺察到嗎?」或是「我所關心的自我到底在哪裏?找得到嗎?」或是「我是否了解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我對事物的了解有沒有因而改變?」在三法印中,除了觀察無常外,我們也可以觀察其他二種:苦與無我。心平靜時,能夠保持客觀,並且能夠放下我們所接觸的二元的、相對的事物。有了平靜的心,我們會放下一些執著,並能更清楚的觀察世事。
以上所說的各種階段,引領我們走上清淨之道,並證得內觀智慧。當然,「於現法中,智慧充廣」是開悟的最後階段,而心清淨是先決條件。如果心不夠清淨,就無法客觀的觀察。禪修使心清淨,所以我們必須禪修。透過一再的修習,不斷的觀察,每個階段的內觀智慧會慢慢增長,而我們也可以隨時應用內觀智慧。
第十二章
何者是真正的自我?
象首加入了對話,並提出有關「自我」的新的問題。當想到「我們是誰」,這種難以理解的問題,象首、布吒婆樓和我們其實都差不多,經常會有新的想法。
時,象首舍利弗白世尊言:
「世尊,粗我得存在時,意所成我得之存在為虛,而無形我得之存在亦虛。此時,唯粗我得之存在為實耶?
世尊,意所成我得存在時,粗我得之存在為虛,而無形我得之存在亦虛。此時,唯意所成我得之存在為實耶?
世尊,無形我得存在時,粗我得之存在為虛,而意所成我得之存在亦虛。此時,唯無形我得之存在為實耶?」
象首問:如果只有一種「自我」,其他兩種又如何?象首認為三種「自我」都存在。我們可能會認同他的看法。例如,當我們走路時,不小心被樹根絆倒,腳受傷,流血了,我們會自言自語:「我的腳受傷了,要馬上處理。」於是去藥房買藥膏塗,但一會兒又痛起來,我們會想:「真的痛得很厲害,看來只塗藥膏是不夠的。」於是去按摩或針灸,或做其他的治療。這時候我們所認同的自我是「粗我得」,以身體為自我。此經的翻譯比較學術化,用「粗我得」是為了符合巴利文的原意,為了使意思更清楚,我們有時也用其他的翻譯。
我們經常以自己的身體為「自我」,例如,吃飯時,我們會想:「我肚子餓,想吃些東西。」飯後,我們會說:「好像不太飽,我想多吃點。」我們關心的是「我的」肚子餓,「我的」身體,「我的」胃。
象首問佛陀:這三種自我是否同時存在,佛陀回答:
象首,粗我得存在時,唯名為粗我得,決不名為意所成我得,亦不名為無形我得。
象首,意所成我得存在時,唯名為意所成我得,決不名為粗我得,亦不名為無形我得。
象首,無形我得存在時,唯名為無形我得,決不名為粗我得,亦不名為意所成我得。
很明顯的,我們同一時間只能有一種自我。尤其是當身體感到疼痛或愉快時,我們就會視身體為自我。身體很少有不苦不樂的時候,一旦有較強烈的感受,我們馬上會把身體視為自我。禪修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身體有點不舒服,我們馬上就會關心起來,除非定力非常強,不受影響。我們很容易視身體為自我,一次感冒,一陣咳嗽,「粗我得」立刻生起-是「我」在感冒、咳嗽。
另外,我們也把「意所成我得」(mind-made self)視為自我,例如,我們精進的持戒,就會想:「真好,我一直在持戒。」持戒是好事,但說這話時,我們認同的是甚麼?肯定是「我」,是「我」在持戒,是「我」在想這件事。有時在禪修時,我們的心充滿妄念,無法入定,因此很煩惱。妄念一再生起,我們知道自己有這些妄念,也認為這些妄念是我的。在相對的層次中,我們認為是「我」想禪修,是「我」被這些妄念所干擾,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可能嗎?
這種「意所成我」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也是觀察者和記憶者。例如,我想起了十年前的「我」,有此念頭時,此刻的「意所成我」想起了另一個「意所成我」,所以有兩個意所成我。當然我們不這樣認為,我們會說:「有人正在回憶,那個人就是我。」我們忘了記憶只是記憶而己,別無他物。或者我們會向前瞻望,為將來的「我」打算,此時,有兩個「我」存在,只是我們沒有覺察到,我們只知道是「我」在計劃未來。我們知道「為將來打算」會干擾禪修,卻又認為這是愉快的休閒,讓我們暫時忘記身體的疼痛。基本上,「意所成我」是心的作用,是心在說:「這是我。」
事實上「意所成我」總是存在著,「意所成我」從一醒來就出現。當我們醒來時,第一個念頭是甚麼?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正念,或許能覺察到,腦袋本來空空的,突然心理活動開始了:「現在幾點了?我今天要做甚麼?我會遲到嗎?會感冒嗎?」這些都是心在活動,身體只負責張開眼睛,所有這些心理活動都在支持「我」的存在。這個「我」也在找尋脫苦的艙口,於是所有的掉舉、不安、擔憂、計劃、回憶,隨之生起,可惜這些心理現象無法解脫苦,或許能暫時避開苦,所以是一條死胡同。潛藏的苦永遠存在,只要為瑣事操心、不安,苦就會生起;每當我們計劃未來時,就必需面對這些苦,所以我們會想:「今天,我要做甚麼?我要上班,之後,要好好散步,或約朋友一起用餐。」
我們最關心的是「意所成我」,意所成我是三種「自我」中最難去除的,我們可能認為:「我知道這些道理。」而誰是那個知道者(knower)?拉瑪那.馬哈希(Ramana Maharshi)是南印度已開悟的聖者,於五十年代去世,他的教法非常簡單,只問:「我是誰?」這相當難掌握,我們可能需要準備或透過其他的訓練,甚至要花好幾世的時間。他的弟子尼薩迦達他(Sri Nisargadatta Maharaj)只教導「我是這。」(I am that.)以及放下所有事物。
修行最後都會回到一個重點,佛陀以聽眾可以接受的方法指出這一點:如果想追求真正的快樂,唯一的方法是放下那個不快樂的人,而不是執著那個快樂的人。當那個不快樂的人消失了,就會有由平靜及純然的覺知所生起的快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許多機會來觀察這「意所成我」,例如:「明年我要做什麼?我要去哪裡?怎樣處理才合我心意?」心不停的攪動,追尋,無法平靜下來。
了解這些,並非指我們能去除「意所成我」,但已經向前邁一大步。如果我們無法覺知「意所成我」,就會隨著本能或衝動行事,永遠是凡夫,只會跟隨大眾行動。雖然我們沒有任何不滿,但仍會逃避苦,因此心無法安住在當下,一旦心想逃避現實就會產生苦。當我們發現這是「意所成我」的作用,心就會安住在當下,所以要先知道心的狀態,然後再採取行動。
當我們能覺知「意所成我」時,就會生起另一個層次的認知(recognition)。這並不是說:我們能立刻去除「意所成我」,但已經接處到邊緣了。在去除「意所成我」之前,去觀察我們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在想,我在觀察,我很專注,我的心不夠專注。」這些都和「我」有關,可以歸納為三種:「我現在…」或「我將…」或「我已經…」。
佛陀說:
象首,設若有人,向汝問言:「汝曾存於過去世,汝非已有否?汝將存於未來世,汝非當有否?汝存於現在,汝非今有否?」象首,有如是問者,汝云何答?
世尊,有如是問者,我當答言:「我曾存於過去世,非不存在;我將存於未來世,非不存在;我現在存在,非不存在。」世尊,於如是問者,我當如是答。
象首和我們一樣,認為他的「自我」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存在。這些都不是新的論調,佛陀會教他完全不同的法。
對過去、現在、未來的「我」,人們有許多設想(assumption)。首先,我們在劃分界限。「過去的我」存在回憶中;「現在的我」很少被觀察到,我們隱約感到它的存在,卻難以窺知;我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未來的我」,未來的我會做許多美好的事,會比較快樂,能夠入定等等。我們把這三個「自我」都稱為「我」,而實際的情況則更複雜。當我們把過去帶到現在時(即回憶過去),過去的我就變成現在的我。同樣的,當我們把未來的我帶回當下,那麼未來的我就變成現在的我,所以我們不但把自我劃分成三個,也把時間劃分成三部份。結果是,我們的生活並不完美,因為活著就有體驗(苦樂參半),而我們唯一能體驗的是當下這一刻,其他的不是記憶就是希望。
把自我和時間分成三個部份後,我們發現:我們焦慮的期待未來,或充滿懊悔的回想過去,因此快樂離我們而去。每當我們把自我分成三個部份,便沒有空間讓快樂生起,雖然有可能生起樂趣(pleasure),但這不是快樂。快樂與內心的喜悅、平靜有關。把自我分成三個部份並不能產生平靜。然而,既然大家都是這樣過生活,所以我們無法覺知這是徒勞無功的,是多麼的虛幻。我們一直認為生活就是這樣,直到接觸佛法,我們才知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透過正念和禪修,我們可以覺知當下的身心狀態,儘管只是片刻,我們都能體會活在當下的滋味。過去的已過去,未來的尚未到來,只有當下可以掌握。
象首和我們一樣,仍然執著由時間所劃分的「自我」,佛陀試著以比較邏輯的方法,讓他看到真相:
象首,又若問汝:「汝存於『過去我得』時,唯汝之『此我得』為實,而未來(我得)為虛,現在(我得)亦虛耶?
復次,汝將存於『未來我得』時,唯汝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我得)為虛,現在(我得)亦虛耶?
復次,汝存於『現在我得』時,唯汝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我得)為虛,未來(我得)亦虛耶?」象首,有是問者,汝云何答?
世尊,若問我言:「汝存於『過去我得』時,如是乃至汝存於『現在我得』時,唯汝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者為虛,未來者亦虛耶?」
世尊,有是問者,我當答言:「我存於『過去我得』時,唯我之此我得為實,而未來者為虛,現在者亦虛也。
復次,我將存於『未來我得』時,唯我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者為虛,現在者亦虛也。
復次,我存於『現在我得』時,唯我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者為虛,未來者亦虛也。」於如是問者,我當作是答。
聽了佛陀的解釋後,象首知道不可能有三個「自我」同時存在。現在,他認為只有一個「自我」存在,分別是過去的自我,現在的自我和未來的自我;之前,他以為有三個自我,現在只剩一個;而大多數的人認為我們有三個「自我」。
如果我們看以前的相片時,我們看到甚麼?除了朋友外,就只有過去的「我」。這也是我們拍照的原因:過去不會隨著時間消失。我們會說:「這是我。」我們和象首開始時一樣,將「自我」分成三個部份;如果加上身體和心就有五個「自我」;如果再加上時間的話,「自我」隨著時間又分成:久遠的過去,不久的過去,昨天等,那麼就會有數百個過去的「我」,就像相片簿中的照片一樣。最後「我」多得連自己也數不清,究竟哪個「我」是自己。如果佛陀問我們同樣的問題,我們也會和象首一樣回答,我們知道不可能有數百個「我」同時存在,甚至連三、四個「我」都不可能,最後我們會說:「只有一個我,就是當下在覺知的那個。」
象首知道不可能有三個「自我」同時存在,只有當下的「自我」存在。想想看有許多「自我」消失在過去,而有許多「自我」在未來出現,我們想想就知道這是很荒謬的,是不可能的,由於我們不知道還有其他的說法,所以只能接受這種說法。
過去有些神秘學家有不同的體驗,也知道這種自我觀的謬誤之處,他們知道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它的原因只有一個:「有愛」。如果我們能去除「有愛」,就不會有類似的煩惱。看破有愛的方法是去觀察「自我」如何使「有愛」生起;也可以看看「有愛」如何使「自我」生起。兩者是同生同滅,所以不能說哪個先,哪個後。
象首知道他就是當下的這個「自我」,我們或許同意這種看法。他現在仍有「無形我得」要處理,「無形我得」是我們的意識。既然我們不是身體,也不是心,那麼我們一定是意識了。有一種意識是在禪那中的意識,因此這種禪那也稱為世間禪那,而非出世間禪那,因為仍有「自我」。
所有的禪那都有同樣的性質:有時強,有時弱。前三個禪那的「自我」非常明顯,第四禪就比較不明顯,第五至第七禪比較強,只是層次不同,是比較高超的意識,但「自我」仍存在,仍在覺知這些禪那。在第八禪,自我意識變得非常弱。我們知道:在禪那時,身體意識是不存在的。另外也沒有「意所成我」,如果有任何念頭,禪那就會終止。在禪那中有一種高超的意識,我們喜歡認同這種意識,因為這種意識是最令人滿足的,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因為有些人做不到。很明顯的,這種意識是某人的,也就是「我」的。
退出禪那後,有另一種意識存在,也就是「我知道當下發生的事。」我們通常稱之為觀察者,這種意識是我們強烈認同的自我意識。如果我們放棄以身體為「自我」,或放棄以心的四個層面(即受、想、行、識)為「自我」,我們會發現仍有某種東西叫做「自我」。
我們的「有愛」會說:「如果沒有我,我(有愛)就會消失。」所以我們選擇更微細的「我」-意識,這就是「無形我得」。在理智上,我們或許會放下其他兩種「我得」,事實上可能甚麼也沒放下。如果像象首一樣被問及,我們可能會和他一樣訴諸「觀察者意識」。我們認為,這種觀察者意識和其他的心的狀態不同。有感官意識,有感受、想、行,而觀察者被區分出來,以便觀察其他的心理狀態,我們卻忘了「觀察者意識」也是心識作用的一部份。
象首接受只有一個「自我」存在,並能於當下體會。他同意有三個我:過去的「我」,現在的「我」和未來的「我」。佛陀接著為他解釋:
象首,譬如由牛有乳,乳變為酪,酪為生酥,生酥為熟酥,熟酥為醍醐。當有乳時,唯名為乳,決不名酪,不名生酥,不名熟酥,不名醍醐。當有酪時,乃至有生酥時,乃至有醍醐時,唯名醍醐,決不名乳,亦不名酪,不名生酥,不名熟酥。
象首,此亦如是,「粗我得」存時,決不名為意所成我得,亦不名為無形我得,唯名為粗我得也。
象首,「意所成我得」存時,決不名為粗我得,亦不名為無形我得,唯名為意所成我得也。
象首,無形我得存時,決不名為粗我得,亦不名為意所成我得,唯名為無形我得也。…
象首,凡此等等為世間共相,世間言語,世間名稱,世間記述法,如來用之,正當者也。
在這裡,佛陀有很重要的開示。佛陀告訴象首:這是一般人所說的和所相信的,而就絕對層次而言,並非如此,因為人們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佛陀能看到實相,並以世俗的語言表達,不會誤用。由於布吒婆樓和象首一時無法掌握絕對層次的法,所以佛陀只用相對層次的語言來說明,佛經中經常提到佛陀會按照聽眾的能力來說法:
我佛無上師,所說二諦者。
真諦與俗諦,而無第三諦。
俗諦世間用,於世而為真。
真諦無上諦,於法而為真。
佛為世間解,用而無妄言。
世俗層次的語言並非妄語,而是我們如何看事情和互相了解的方式。然而有其他的方式,也就是絕對的層次,諸法實相的層次。當Dhammas中的d和s是小寫時,指現象;當D是大寫,而沒有s時,指佛陀的教法(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真理或自然的法則。
如果象首能了解只有一個短暫的「自我」存在,佛陀就已經很滿意了。佛陀為象首舉了將牛奶釀成酥的比喻,希望他能了解在同一時刻,我們只有一個「自我」。佛陀的說法到此為止,佛陀並未說明:在絕對的層次,連這個短暫的「自我」也是假象。佛陀知道,首先要讓象首和布吒婆樓邁向修行的道路,否則,他們只會停留在知性的層面,繼續找新的話題來辯論,最後將一無所獲。因為去問「什麼是自我?」,「為什麼沒有自我?」,「為什麼我們不能得到所喜歡的自我,而不是我們不喜歡的?」這些問題無法生起內觀智慧。希望有個自己喜歡的「自我」,這種想法與靈魂的觀念有關,也是另一種「我見」。我們視靈魂為良善的「自我」,而不喜歡的部份就不是「自我」。所有人都曾墮入類似的陷阱,在這問題上,世人都是一樣的。
現在經文即將結束,傳統上經文末段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因為佛陀入般涅槃後的二百五十年間,經文都是靠口口相傳的,之後才以文字記載,所以經文結尾都大同小異,以免有任何錯誤。
世尊如是說已,布吒婆樓苦行外道曰:「偉哉世尊!大哉世尊!猶如使倒者得起,閉者得開,迷途者示之以道,冥室燃燈,有目得視。世尊以無數方便,說示教法,亦復如是。世尊,我今歸依佛陀,歸依法,歸依僧眾。唯願世尊,聽攝受我,自今已後,盡壽歸依,為優婆塞。」
在此處,布吒婆樓已經完全信服佛陀所說,並希望成為在家弟子,皈依佛、法、僧三寶。皈依表示投入修行,護持和信受佛法,表示已經找到情感和心靈的庇護所,能帶來極大的喜樂。今天我們也同樣皈依三寶,只是布吒婆樓能見到佛陀本人和皈依佛陀。佛陀是位歷史人物,和我們一樣是人,經過修行後,證得正等正覺。皈依佛,就是以熱誠、敬愛和感恩的心來接受這些事實。我們也皈依法,皈依法是以「法」作為生活的指導和獲得幸福的最高原則。我們也皈依僧伽,皈依那些已經開悟的僧眾,以及已經弘揚佛法逾二千五百年的僧眾,他們使佛法能留傳至今。
當我們皈依三寶時,充滿感恩、熱誠和投入。如果我們能依法修行,並了解佛法的話,我們可以避免來自世間和自己本能(instincts)的危險。皈依可以使我們堅定不移,使我們繼續修行。大部的人很難堅持修行,因為必須從世俗的工作中抽出時間,所以常常是斷斷續續的。
有些東西比我們偉大多了,記住這點對修行很有幫助,因為謙虛感會在心中生起,這和自卑完全相反,自卑意味著「我比你差」;而謙虛是指我們知道「我們並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麼重要」。謙虛是朝向「無我」的重要一步。有些人自認為很重要,而一個謙虛的人就不會如此。只要我們覺得自己很重要,就不可能放下「自我」。謙虛是修行的一部份,使我們能如實的了解自己。謙虛的人不會自責,不會感到自己沒有價值。真正謙虛的人會知道自己是凡人,會有凡人的愚蠢。即使在表面上,我們不再做一些愚昧的行為,由於我們的心仍然不夠清明和完美,所以難免有一些愚蠢的念頭。當我們認識到佛陀的究竟清淨和謙虛,就會受到啟發,並向他學習。
布吒婆樓就是這樣,他發願「盡形壽」皈依三寶。當我們皈依佛、法、僧三寶時,切莫半心半意的,或只是一時興起就去皈依。我們皈依是為了在生活中實踐。
此時,象首也有話要說,一開始和布吒婆樓說的一樣:
偉哉世尊!大哉世尊!猶如使倒者得起,閉者得開,迷途者示之以道,冥室燃燈,有目得視。世尊以無數方便,說示教法,亦復如是。世尊,我今歸依佛陀,歸依法,歸依僧眾。
接著,象首又說:
唯願世尊,許我等於世尊所,得出家受具戒。
象首請求成為比丘〈bhikkhu〉。那時候出家是件容易的事,佛陀只要說「善來比丘」就行了;現在出家有許多儀式,還有許多戒律。早期的僧伽並沒有戒律,因為沒有比丘有不當的行為,由於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僧團,情況改變了,每當有人犯錯,佛陀就會制定新的戒條,日積月累,由75條至115條、150條,最後有227條。假如佛陀活在今日社會,可能會制定更多戒律。
有些戒律已不適合現代社會,畢竟二千多年前的印度社會和現在的西方文化有很大差異,當然,一些重要的戒仍然有效,而一些小戒已經不合時宜。佛陀制戒非常仔細,函蓋了生活上的每個細節,例如有些戒律規定比丘如廁時,要小心,不要傷害小動物。當佛陀無法親自處理每件事時,就制定出家儀式讓人遵守,讓一些夠資格的長老代替佛陀主持出家儀式,這些儀式和現在的差不多。
於是,象首舍利弗,於世尊所,出家受具戒。
出家,指由在家生活轉變為無家的生活,不是要住在沒有屋頂遮頭的地方,而是不再有家庭生活,不再有私人財物。有段時間僧伽的確沒有任何地方可住,後來才有寺院,出家人才有茅蓬(kutis)可住。
受具戒後,尊者象首舍利弗,即獨處,心不放逸,慇勤專念,精勤止住。為良家子出家所求最上梵行之究竟道,彼為時未久,即於此時,自身證得超越之智,安住其中,自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生已盡,梵行已立」,修行到了極致時,不會感到在身心中有個人,有個體存在。如果我們沒有這種體驗,我們不可能知道這種感覺,然而我們可以推知:不再有「我」,所以沒有「我」在擔憂,在計劃、在回憶和需要安全感,只有身和心去做一些該做的事而已。佛陀說法四十五年,也是處於這種狀態。「生已盡」是因為「生」是由「有愛」所引起的,而有愛是由「我」引起的。如果沒有「自我」,就沒有貪愛,也不會再生(rebirth)了。正如婆蹉衢多的故事一樣,沒有木柴,火焰自然會熄滅。最後,經文提到:
尊者象首舍利弗,成阿羅漢。
象首是大象訓練師,在當時的印度是收入豐厚的職業,斯里蘭卡語是mahout,即使現在仍是非常重要的職業。經中經常提到「良家子」,這並非指那個人來自富有或較高種姓的家庭。佛陀不重視種姓,任何種姓的人都可以成為佛陀的弟子,都可以出家,例如掃街的人或理髮師,這兩種人在古印度是階級很低的,而佛陀也會讓他們加入僧團。佛陀認為:最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內在修養,而不是他的種姓。所以「良家子」指此人來自一個善於照顧小孩的家庭。
經文告訴我們,出家的目的是要成為阿羅漢,象首知道「即於此時,自身證得超越之智,成為阿羅漢-這是最上梵行之究竟道」。在經中,不再提及主角布吒婆樓,我們只知道他皈依了,希望他也在修行。而在經文結束前出現的象首是完全獻身於修行。
以上經文的結尾是大部分經文結束的方式,也就是以「有人請求出家」來結束經文。
縱觀全經,我們知道要改變一個觀念錯誤的人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佛陀親自出馬也不例外。「自我感」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已根深蒂固,讓我們很容易執著身體、心或意識為「自我」;或執著過去、現在、未來的「我」。那些喜歡思辯的人會去分析和思考此經,然而,他們將一無所穫。當然也有人甚麼也不做,因為他們看不出修行有甚麼利益,所以他們會放下這部經。
雖然本經的小標題是「心識的各種層次」,而事實上是在討論「自我」的意識。
第十三章
道及果:修行的終點
《布吒婆樓經》從修行的起點說到修行的終點,詳細指導應如何禪修,分別是持戒、修定及修習內觀智慧禪,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遵循這些指導的成果。最後生起的內觀智慧能觀察「自我」的虛幻不實,進而徹底放下自我。
在這部經中,我們知道不可能有許多「自我」,每一刻只有一個「我」,生起又消失,新的我又出現。首先出現的是以身體為「自我」,把身體視為「我」;然後,意所成我(mind-made self)會出現,這是把心理活動視為「自我」,當我們的意識執取某種事物時,這種意所成我也會消失。這些「自我」都是不穩定,不可靠的;無論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我」都是不堅固的,都會消失。片刻之前我們有個「自我」,現在我們有另一個「自我」。我們可以回想之前的那些「自我」,並問自己:那些過去的「自我」現在在哪裡?就如想起自己曾做過某件事,而那件事現在是不會再做的。那麼究竟哪個「自我」才是真的?是過去的我或現在的我?我們永遠無法抓住「自我」,因為自我經常在變動。自我就像一條小溪,如果我們想抓住溪水,我們把手放到水裡,試著去抓溪水,將一無所穫。溪水不斷流動,如果不流動的話,那麼就不是流水,而是一潭死水。
當我們知道「自我」是假象,並了解其性質時,就需要不同的方法來修行。有些人透過覺知「苦」來觀察自我,厭惡自己的苦,所以每當「自我」體驗到苦時,就能放下「自我」。有些人則看到自我中無常的特質,也就是剛才所說的。有些人則會分析「自我」為何物,他們發現自我是不真實,不堅固,不可靠的。有些人則同時用這三種觀法,也就是觀察自我的特質-無常、苦和無我(沒有實體),這是內觀智慧禪的精髓(essence)。
在修行時,把無常、苦、無我這三法印銘記在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世俗的生活中,許多事物看起來好像是恆常的,能夠帶來滿足;好像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可界定的個體。所以世俗的生活對修行沒有幫助。我們必須記住這三法印,並用來觀察我們的身心,觀察我們的感官經驗和所有的念頭。如果忘了去觀察,就等於忘了修行。
修行不只是禪修而已,雖然禪修是修行的重心,如果不禪修的話,心會堅如磐石,很難改變。除了禪修外,我們也要觀察自己的心念和隨之而來的行動。看看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確?是否看到苦的實相而想離苦?還是想尋求短暫的快樂來逃避苦?我們選擇哪一種?如果想要知道實相,我們必須去尋找。我們的心好像圍了一層面紗,一層霧或一道磚牆般,難以窺見。我們或許是禪修者,但仍然是凡夫(puthujjana),也就是尚未證得「道」與「果」的凡夫。「道」與「果」是精進修行的結果。
道心(path moment)巴利文是magga,道心生起後會生起果心(fruit moment),巴利語是phala,合稱為道果(magga- phala),是我們修行的目標。當道心與果心生起時,禪修者會有很大的改變,會成為聖者(Ariya),是真正的佛陀的弟子。
我們怎樣才能證得「道心」?除非我們修習禪那和內觀智慧禪,並勘破「自我」的虛幻不實,這指我們必須從基礎修學起,這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一種事實,對於解脫之道我們沒有絲毫的懷疑,否則不能證得道智。我們相信所謂「自我」只是一種概念而已,其他人相信與否與我們無關。我們可以自問:「那些相信有『自我』的人快樂滿足嗎?抑或他們的『自我』的觀念正是痛苦煩惱的根源?」當我們深信無我,就會放下虛妄不實的自我,證得道心時,便能做到;放下自我並不容易,但至少我們知道要如何放下。
獲得道心的最佳時刻是禪那後,佛陀說在任何禪那後都可以證得道心,而三禪、四禪、五禪、六禪及七禪最適合,因為此時的心特別平靜,沒有五蓋。當五蓋生起時,我們無法看清實相,剛退出禪那,沒有五蓋,心特別平靜清明,能夠體驗到不同層次的境界。事實上,在修習安止定後,除非入定的時間很長,心非常平靜、穩定,否則五蓋仍會生起,這時是不可能證得「道智」的。所以內心不受干擾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知道心中沒有五蓋時,我們可以再度觀察自我的三種特性(無常、苦、沒有實體),直到了解「自我」只是假象罷了,除了假象外,別無其他,然後看看我們是否願意放下這由感受及意識組成的「自我」。當心毫無疑惑,能了解自我是一切苦的根源,而自我會不斷改變,並沒有不變的實體;同時也知道:放下自我是修行的目的。
接著我們可以作意,把心導向寂止(still-point),此時心沒有任何活動,處於寂止狀態。心必須沒有五蓋,沒有任何疑惑,例如,「或許是『我』想去除某些東西」,若有這種念頭,心就無法平靜。如果心是平靜的,自然會寂止,此時沒有任何心理活動,所以也沒有體驗者(experiencer),我們無法敘述道心,只能說此時所有的心理活動完全寂止。這和第七禪「無所有處定」的體驗有所不同,因為在禪那中,仍有一個體驗者,體驗到一切法中並沒有固定不變的事物,而當道心生起時,一切寂止,連體驗者也不存在。
緊隨「道心」而起的是「果心」,由於「果心」有某些特性,可以用語言表達,有經驗的老師可以以此來判斷弟子的修證境界,看看弟子是己經證得,差不多證得,或只是想像出來的境界。並非所有的特質都會出現在每個人每次的經驗上,但有些特質總會生起。證得果心時,會大喜,充滿喜悅,會有完全的解脫感,就像我們放下巨大的負擔一樣。這種解脫感非常強烈,可能會使我們流淚,這不是傷心的淚水,而是從巨大的壓力、苦迫中解脫出來的感覺。這種喜樂的感受可能稍後才會生起,雖然果心隨著道心立刻生起,而大喜則未必立刻生起,可能在第二天,當心再度體驗解脫時才會生起。
當道心與果心生起時,智也會生起。例如,在某一時刻,沒有人存在,而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最深湛的智。在第一次證得果心時,這種體驗特別明顯,因為那時「自我」完全消失。
我們知道一個心識剎那(a mind-moment)是多麼短暫。「覺知」與「解脫」佔去兩個剎那,最多不超過三個剎那。那種解脫感、自在感以及伴隨的淚水,如果沒有立刻生起,稍後可能會變成大喜。而「覺知」會立刻生起,我們會知道剛才所發生的事,並了解修行所為何事,有時會感到身體失去重量,身體好像輕了許多,這是因為心「輕」了,影響到身體。
西元五世紀,覺音尊者在斯里蘭卡編纂的《清淨道論》是一本非常厚的書,此書總結佛陀有關修行的教導。這本書不容易讀,因為非常詳細,卻是本非常有用的參考書,而且有許多譬喻,其中有個過河的譬喻形容得非常貼切:
覺音論師提到一條河,河的兩岸分別代表世俗生活與涅槃。靠近河岸有一顆巨大的樹,樹枝上有條繩索吊著,人拉著繩索就可以從世俗的河岸吊到涅槃的彼岸去。樹枝代表我們對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以身體為自我。在修行過程中,當我們想起「我」在修行時,這是以色身為我;而那條綁在樹上的繩索代表自我的觀念。我們抓著繩索,用力把身體搖到對岸,這代表修行。當衝力足夠時,在適當的時刻,如果我們能夠放下自我,就會降落到對岸去。
這只是一則譬喻,卻非常有用。當我們落在對岸,剛開始會立足不穩,因為這是以往從未遇過的新處境,所以必須穩定下來。在體驗過道心後,我們會感到心神不寧,好像發生重大的事情,卻難以形容,因為既不樂,也非不樂,這種情況並不罕見。有些人就很穩定,而有些人要一兩天才回過神來,有些人則需要老師的幫忙。然後,我們就可以快樂的欣賞彼岸的風光。我們已經變成不同的人,表面上我們和以前完全一樣,除了我們的老師外,可能沒有人知道我們內心的變化,只有自己知道。
初次證得道智及果智(初果)時,自然會破除十結中的前三結。佛陀說:這十結使我們不斷的生死輪迴,這十結包括:一、身見(我見);二、戒禁取見;三、疑;四、貪;五、嗔;六、色貪(有愛);七、無色貪(無有愛);八、慢(conceit);九、掉舉;十、無明。這十結把我們束縛在有為法中。佛陀把他兒子命名為羅睺羅,意為「結」(fetter)。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這些結,使我們能究竟解脫。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結」是身見。去除身見以後,我們不再相信有個「自我」透過我們的眼睛去看,耳朵去聽,透過我們的心去想,透過我們的欲望去渴求。我們不相信的理由,是因為我們已經證明「自我」是錯誤的認知,是一種假象。只有證得初果,有第一種果心的人才有此正見。雖然內心的感受有了戲劇性的轉變,但仍未將內心深處的自我感去除,但稍後會做到。當初果聖者自問「我是誰」時,會知道身心的活動並沒有「自我」,也知道「自我」是由貪愛所生,而貪愛就是苦,而自我的觀念是一切苦的根源,世人也因此受苦。
證得初果的聖者,身見或我見永遠不會再生起,當我們在行走時,或與人交談時,仍然有個「人」在那裡的感覺。證得初果後,我們必須把有關自我的正見盡可能銘記在心,尤其是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時,因此時的我執比較強烈,如果忘失了這最深湛的內觀智慧,那麼就會有負面反應,因為證得初果,貪與嗔仍未斷除。提起正見(right view)是修行不可或缺的要素。
證得初果的聖者稱為須陀洹或預流者,指已經預入聖者之流,不會退轉的人。經中提到須陀洹最多再輪迴七次便可究竟解脫,甚至可以在此生證得涅槃。證得初果的人,對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特別敏感,知道心中仍有貪與嗔,並下定決心繼續修行,以斷除其他的煩惱,因此修行又有了動力。
預流者也已去除另外兩個結,其中一個是疑。疑是修行的障礙,使我們不去做該做的事,思索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做,我們浪費許多心力和時間,甚至放棄修行。當我們首次經歷道心及果心,對佛法就不會有任何疑惑。所有對佛、法、僧的疑惑會完全消失。佛陀所說的「無我」,現在我們已經親自體驗到了,這種經驗是非常美好的,且遠遠超過任何安止定的經驗。我們信心十足,感恩,並有強烈的決心。
經中提到佛陀坐在菩提樹下,在一次的禪定中證得四種道心和果心,包括初果(須沱洹),二果(斯陀含,一來者),三果(阿那含,不還者)及四果(阿羅漢)。對我們而言,能證得初果是偉大的成就,而證得初果的聖人很少會就此停住,因為心可以繼續向前。另外一種疑惑是懷疑自己的能力,這種疑惑也已去除,由於我們有超越一般意識的經驗,所以會充滿自信。
自信不是一種優越感,優越感通常隨著自卑感生起。此時所產生的自信是一種內在的力量,毋需向任何人證明,因為既然無我,也就沒有事情需要證明,也無處可去,因為沒有「人」存在。這種內在的肯定能幫助我們去修行,並對佛、法、僧三寶生起信心和熱誠。
預流者所斷除的第三個結是戒禁取見(the belief in rites and rituals)。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相信藉著某些儀式可以淨化我們自己,甚至使我們解脫苦。雖然佛陀否認宗教儀式有這種力量,在佛陀時代的印度和現代社會,這種戒禁取見仍廣為流行。證得初果後,我們會完全捨棄這種錯誤的觀念,因為證得初果是修行的結果,和宗教儀式毫無關係,而與我們的心是否清淨,是否願意放下自我有關。
去除「戒禁取見」並非指我們不再做任何儀式,而是我們不願意浪費太多時間和精力在宗教儀式上,所以會把宗教儀式減到最少。如果以正念去從事宗教儀式,有些儀式的確有淨化心靈的作用,例如誦經或禮敬佛、法、僧,但我們必須要有正念,而不是以刻板的形式來進行這些儀式。誦咒(mantras)亦然,如果我們很專注虔誠的在唸誦,就不會有負面的心態;如果只是機械式的進行宗教儀式,我們可能一邊誦經,而心中卻充滿不好的感覺。
證得初果後,我們的心會比以前更敏銳,因此更能覺知貪與嗔的生起。當貪與嗔生起時,我們發現貪與嗔更令人煩惱。之前,幾乎不會干擾我們的隱微的不善心境,現在變成大的干擾。事實上,這對我們的修行是一種激勵。所以修行不只是在表面上應該有正當的行為,還需要不斷淨化我們的心。
等到時機成熟,才會從初果道心進入二果道心,通常這需要一段時間,尤其是過世俗生活的人,因為世俗的生活、心態、習俗和社會行為(conduct)與此相反,不支持這種修行,所以我們必須有堅定的信心。
證得二果,我們有兩件事必須牢記在心,也就是有關自我的正見與果心。此時,雖然沒有第一次證得道心與果心時的大喜和解脫感,但我們仍需盡可能的使這種喜悅與解脫感生起。
另外,觀察五蓋的生起也很有幫助,看看哪個蓋比較強,哪個蓋已減弱。證得初果,五蓋中的疑已經消失。五蓋中的前兩個蓋是貪與嗔,我們要觀察貪與嗔的生起;也要觀察第三和第四個蓋,即昏沉睡眠與掉悔。我們不斷的問自己:「現在哪個蓋最強?是如何生起的?」不斷的觀察五蓋,才能減輕它的影響。當然,無論在修行的哪個階段,我們都應該如此觀察,同時必須了解五蓋是每個人都有的,只有透過修行才能去除五蓋。如果我們能夠覺察到自己內心的不淨,也許就不會再責備他人。
預流者能覺知到這點,不會把五蓋的生起歸咎他人。他們觀察身心的生滅現象時,發現並沒有「我」在其中,所以沒有人可以歸咎。尚未證得初果的人很難做到這點,因為我們通常不想知道自己的負面情緒。
據說證得初果的聖者不會毀犯五戒,也就是不殺生戒,不偷盜戒,不邪淫戒,不妄語戒,以及不飲酒和吸食麻醉物品戒。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應該觀察自己是否能受持五戒,而不是把它視為一種束縛,而是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
以上所說的都與省察智(reviewing knowledge)有關,省察智在退出禪那時特別有用,因為此時的心非常清淨、清明,最有利於重溫果心,重新省察我們對自我的認識。我們必須一再的審察,直到完全了解「自我」的虛幻不實,使我們不再珍惜自我為止。這不表示我們會自責或想去改變它,而是知道「自我」這概念是想出來的。我們必須觀察一切事物和我們的感受,看看我們的心是否願意放下這個由身心組合的自我,是否願意徹底去除「自我」,沒有任何保留,任何與「我」有關的念頭是否會再生起,因為如果有自我,就會有不良的後果。在這個階段,自我感仍會生起,會妨礙修行。和以前一樣,我們可以讓心寂止,可是我們試了許多次,心仍無法寂止。果真如此,我們必須去觀察我們執著的是什麼,可能有很多東西,經過分析後,我們仍不願意放下那個正在體驗(experience)的覺知者,也就是「自我」。
剛開始,修行的動力可以把我們帶過河。為了重新體驗解脫的境界,我們必須放下所有與「自我」有關的事物。如果仍執著人類的生活,無論是感官欲望、性慾,或其他事物,我們很難進步。所以我們必須下定決心找出「是什麼東西使我如此執著,不肯放下?」如此觀察後,我們會發現:如果我們執著某人,這種執著會使我們變得依賴和憂懼,因為那個人可能隨時消失,我們的執著只會帶來更多的苦。
如果我們執著某些欲望,我們會發現任何欲望的滿足都是短暫的,沒有多久,心又會再度感到空虛,欲望需要一再滿足。這是我們觀察我們的執著的方法,我們想了解實相,而有些人不願意太深入,這當然沒問題,在修行道上,如果我們已經站穩腳步,就一定會向前邁進,繼續證得各階段的觀智。
證了初果後,凡是邁向下一步的聖者稱為一來者,意指證得此果位的聖者,在今生生命結束後,只會再來欲界一次。證得初果及二果的聖者,都會將所證得的道智及果智帶到下一生,所以這些人對我們大有助益,因為他們擁有豐富的經驗和智慧,可以教導我們。
證得二果後,貪與嗔會減弱,但並未根除。「嗔」會減弱為厭煩,「貪」會減弱為喜好(preference),二果聖者的心不會被貪嗔所動搖,因為厭煩與喜好只會在某種程度影響心,比起嗔來,厭煩對心的影響時間較短,而厭煩與喜好比貪嗔要溫和得多。證得二果的聖者會用省察智來觀察,也會發現厭煩與喜好仍然會產生苦。
一來者(二果聖者)所經歷的道心與初果相似,但並非相同,也很難用言語表達;接著會生起類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果心。證得初果時,那種心神不寧的感覺不會在證得二果時生起。此時內心有完全解脫的感覺,通常不會流淚,可以說是大喜,雖然大喜不會立刻生起。心再度寂止,即無所有的境界,這種經驗很真實。在這種境界中,身體、樹木、房子、車子、道路、灌木和高山並非消失了,就相對層次而言,它們仍然存在,就絕對層次而言,它們只是一堆由能量聚合而成的分子,聚合又分散;它們聚合成某種形式,形成各種現象。無所有的境界就是:在一剎那間體驗到一切事物變為碎片,而不再經歷生起的境界。
在證得道心與果心前,我們必須先證得不同的內觀智慧 。首先知道我們是由身與心所組成,身與心並非一體,只
是互相依存(這是名色分別智)。其次,一切現象的本質是生起後必定會消失(這是生滅隨觀智)。接著,我們會觀察到一切現象都會壞滅(這是壞滅隨觀智)。當我們看到壞滅的現象時,除非我們已經證得道心,否則可能會心生怖畏(這是怖畏現起智)。如果心生怖畏,就要向老師請教,並獲得勇氣。我們必須知道:修持內觀智慧禪法,這種怖畏是修行的一個階段,不是出了差錯。在修習內觀時,我們也了解身與心的因果關係,如我們在《布吒婆樓經》中所看到的,身體由四大組成,由食物所養,所以四大和食物是因,而身體是果,我們必須如此觀察。
在修習內觀智慧禪時,有了怖畏的體驗後,又把它放下,此時,會迫切的去修行,並希望能解脫(這是欲解脫智)。接著,出離心與離欲使我們能證得道心,證得道心(道智)後,我們能如實的了知事物的真相。隨之生起的果心(果智)使我們不再懷疑所經歷的,而每一刻的果心會越來越強,之前的果心通常會在記憶中消失。所以我們對剛生起的果心會有最深的印象,因為它會帶來大喜與解脫。
事實上,很少人能體證道心,對此我們不應感到意外。因為大部份的人都受貪與嗔的影響,我們要經歷兩次的道心,才能使貪與嗔減弱。在去除貪與嗔之前,我們仍須不斷的禪修。
證了二果後,我們還有兩個階段要完成。這兩個階段顯然是最難的。我們必須完全放下自我,使貪與嗔完全消失。再經歷一次道心後,貪與嗔將被根除,於是前五個「結」全部去除,也就是所謂的「五下分結」全部消失,此時,已證得三果,成為不還者,意指此生結束後,不會再回來人間。證得三果並不容易,即使證得三果仍有五個結需要斷除,才能證得阿羅漢果,此時「自我」才完全根除。如果三果聖人於死前未能證得阿羅漢果,由於仍有色貪及無色貪,就會投生到淨居天,在那裡證得阿羅漢果,這是因為三果聖者仍有五上分結,仍有投生在無色界的欲望。
不還者還有我慢與痴(無明)兩個結。此處的痴指內心深處非常隱微的自我感。「慢」並非指傲慢,而是指自我的「想像」(a “conceiving” of a self)。因為有這兩個結,所以心仍會掉舉,當然這種掉舉與世俗的掉舉截然不同,後者指心不斷的追求外物來滿足欲望。對不還者而言,由於隱微的自我感仍未消失,所以仍未完全脫離苦。修行到了這個階段,要觀察的心理活動變得非常隱微,那些比較粗的「蓋」已經消失,而剩下的掉舉也變得非常微細,一旦覺察到它的存在,就會立刻消失,所以三果聖者仍需繼續修行。
欲證三果的二果聖者應以類似的方法修行,即觀察前三個結(即身見、戒禁取見、疑),肯定它們已經消失,並觀察貪與嗔,肯定貪與嗔已經變薄弱。二果聖者的「自我」遠比三果聖者來得大。當我們觀察自我時,會發現並沒有「人」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仍感覺到有「人」在說話和反應,這是因為仍有某種程度的貪與嗔。因此我們要有正見,重新生起果心,並觀察自我的虛幻不實。這種觀察必須非常徹底和深入,因為證得不還果是極大的轉變,所以必須一再的觀察。這種觀察不只是理智的觀察,而是完全投入,放下一切,所有世俗的事物都要放下。尤其是身心中和「自我」有關的都要去觀察。
此外,必須有極強的決心,那麼(三果)道心就會生起,如以前一般,心又再度寂止,此時,沒有任何念頭;接著果心會生起。在三果道心生起前,由於心已經體驗過兩次的道心,所以這次沒有強烈的感覺,而道心是很短的,而隨之生起的果心只是一種認知,沒有淚水和大喜,只有覺知和清明,以及解脫感:「啊,終於解脫了!」而不再有之前證果時的滿足感,心也非常清楚仍有餘結要斷除。
不還者必須觀察剩下的五個結,看看自己是否仍想投生在較高的天界。不還者有這種欲望,所以會希望一切都是愉快的和宜人的,也就是不想有任何的苦。當然這也是一般人的心態,而三果聖者不止於此。這種心態成為一種內在的動力,希望能投生在只有快樂沒有苦的無色界。這種強烈的感覺也要觀察,而剩下的比較微細的「自我」也要觀察。佛陀提醒弟子們要觀察這欲望,因為投生在無色界的眾生壽命很長,一旦投生到那裏,就會有無數劫的壽命,所以有些天人以為自己的壽命是無限的。在人間,有許多苦來刺激我們修行,而三果聖者所投生的淨居天就完全沒有苦,所以要他們徹底解脫是很難的,所以佛陀說:這種欲望不利於修行。
不還者應更進一步去除剩下的五個結,因為這是應該做的,而不還者也的確感到剩下的五個結中的掉舉仍然是苦;而想投生在較高的天界的欲望雖然非常小,也是苦,而這隱微的,尚未斷除的「自我」也是苦。
修行的最後一步和之前的大致一樣,不同的是,心決定要讓這身心所構成的人完全消失。世上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留住我們,應該做的都已經做了,沒有甚麼事需要做。一如以往,道心是無法用語言文字形容的。四果道心的專有名詞是無生(non- occurrence),因為「不受後有」,不再投生,所以稱為「無生」。
隨之生起的果心就有此感受。佛陀說未曾經歷過此境界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境界非常可怖。事實上,完全的止息會帶來大喜。這種經驗很難形容,就像跌入雲端,接著就在雲中消失一般。證果後,一切已不復舊觀,世上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影響阿羅漢的心。就像和小孩子玩耍般,我們會對小孩子很友善,樂於和孩子們相處,當和他們玩積木時,也會幫他們堆砌城堡,然而我們會對這遊戲認真嗎?如果有人不小心踩到積木,把城堡毀了,孩子們或許會大叫,而我們不會。當然我們也在幫人們建築城堡,有機會的話,我們要告訴他們不值得花時間去建這些城堡,不要太認真。我認為這個譬喻將證果後的心境說得非常清楚。證得阿羅漢的聖者,將「自我」徹底根除,已究竟解脫,可以隨時回到苦完全止息的大喜。
經中記載佛陀證得涅槃後,安住其中,體驗涅槃之樂達七天之久,才決定將所體驗到的和世人分享。這種自我感的完全去除是修行的極致。正如經中所說的,這位年輕、出身良好的年輕人離家出家,修行證果,「所應做已做,不受後有」,最後,甚麼事情也沒有。
三學、七清淨與十六觀智
三學 七清淨 十六觀智
戒學 一.戒清淨
定學 二.心清淨
慧學 三.見清淨 1.名色分別智
四.度疑清淨 2.緣攝受智
五.道非道智見清淨 3.思惟智
4.生滅隨觀智
六.行道智見清淨
4.生滅隨觀智
5.壞滅隨觀智
6.怖畏現起智
7.過患隨觀智
8.厭離隨觀智
9.欲解脫智
10.審查隨觀智
11.行捨智
12.隨順智
13.種姓智(第六、第七
清淨之間)
七.智見清淨 14.道智
15.果智
16.返照智
布吒婆樓經
1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布吒婆樓苦行外道,與苦行外道眾三百人,住末梨園中,提陀迦樹環遶之大講堂。
2 爾時世尊,清旦,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然於其時,世尊念言:「於舍衛城遊行乞食,為時尚早,寧可往旁末梨園中,提陀迦樹環遶之大講堂。」
3 時布吒婆樓苦行外道與諸多侍眾共坐一處,大聲喧嚷,互相詈罵,耽於種種無益議論,即論王、論盜、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論飲、論衣、論床、論鬘、論香、論親戚、論乘具、論部落、論村莊、論都市、論鄉間、論婦女、論勇士、論市街、論瑣事、論亡靈、論餘雜事、論水陸起源,及論斯有斯無等。
4 爾時布吒婆樓苦行外道遙見世尊自彼方來,即令其眾,靜默毋嘩,曰:「諸士,肅靜勿作聲。沙門瞿曇來矣。彼愛沈默,並讚嘆沈默。蓋知吾等會眾沈默,當覺來訪之不虛也。」彼等苦行外道,聞是言已,眾皆沈默。
5 世尊行近布吒婆樓所。布吒婆樓語世尊曰:「善來世尊,吾等歡迎世尊。世尊久不來此。請坐世尊。此座之設,為世尊也。」世尊就所設座而坐。布吒婆樓別取低座,坐於一旁。世尊問布吒婆樓曰:「布吒婆樓,今汝等集此,為何論議?而汝等論議何故中止耶?」
6 布吒婆樓聞是言已,答世尊曰:「世尊,吾等集此,所欲論者,可(且)置之。因此等論,日後易得也。世尊,曩者多有外道沙門婆羅門,集此論議場所,就增上想滅,發論議曰:『增上想滅,云何而起耶?』時有一類,作是說言:『人人皆以無因無緣而想生,無因無緣而想滅。生時即有,滅時則無想。』斯一類者,以如是說增上想滅。餘者,作是說言:『不然,吾友,想實人我也。夫人我,有來有去。來時即有想,去時即無想。』斯類者,以如是說增上想滅。復有餘者,作是言:『不然。實有沙門、婆羅門,具大神通、大威力。其於人也,移想而來,掣想而去。移來則有想,掣去則無想。』斯類者,以如是說增上想滅。世尊,爾時,我心生念。念言世尊:『嗚乎世尊,精通此法。倘於此時,世尊在者,倘於斯時,善逝在者。實因世尊熟知增上想滅者也。世尊,何者是增上想滅?』」
7 「布吒婆樓,彼婆羅門言『人人皆以無因無緣而想生,無因無緣而想滅。』誤矣!所以者何,布吒婆樓,有因有緣,人之想生;有因有緣,人之想滅。由於修習而想生,由於修習而他想滅。」世尊說言:「云何修習?布吒婆樓,今者如來出現於世,如來是應供、等正覺、乃至身業、語業,清淨具足,營淨生活,具足戒行,諸根之門,悉為守護。具足正念正知,自知滿足。
如來出現於世,是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如來於此世界、天界、魔界、梵天界、於此大眾、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自身證悟,而為說示。如來宣說教法,初善、中善、終亦善,文義具足,示教梵行,完全清淨,無與倫比。
若長者,若長者子,若生於餘種姓者,聽受如來教法,彼等聽受已,信仰如來,得信仰故,如是思惟:「障礙哉塵勞家居。自在哉出家生活。專修梵行,完全清淨,耀如螺鈿,若處居家,殊非易事。今我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離家出家。」乃於後時,棄捐財業,捨去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離家出家。
如是出家者,以波羅提木叉禁制,而住持戒。精勤正行,雖於小罪亦見怖畏,受持學處而自修學。身業、語業,清淨具足,營淨生活,具足戒行;諸根之門,悉為守護,具足正念正知,自知滿足。
布吒婆樓,比丘云何具足戒行?布吒婆樓,今有比丘,
捨殺離殺,不用刀杖,懷慚愧心,充滿慈悲,利益一切生類有情,而住悲憫,此為比丘戒行一分。復次,或有沙門、婆羅門,為世所敬,食他信施,然於諸無益徒勞之行,若許願還願,乃至給樹根,施藥料,除藥料等。以此等行,邪命自活,今於是事,皆悉捨離。此亦為比丘戒行一分。
8 布吒婆樓,比丘如是戒行具足,因戒制御,故在在處處,皆無怖畏。如是乃至彼具足聖戒聚,內心無垢,純淨安樂。布吒婆樓,比丘如是具足戒行。
9 布吒婆樓,比丘云何守護諸根之門。布吒婆樓,今有比丘,以眼見色時,不取總相,亦不取別相。彼若無所抑制,則其眼根,隨生貪愛、憂悲、過惡與不淨法。彼御此眼根,以護眼根,令其眼根,歸於制禦;以耳聞聲時,亦復如是;以鼻嗅香時,亦復如是;以舌嚐味時,亦復如是;以身觸所觸時,亦復如是;乃至以意知法(境)時,不取總相,亦不取別相。彼若無所抑制,則其意根,隨生貪愛、憂悲、過惡與不淨法。彼御此意根,以護意根,令其意根歸於制禦。此諸聖根,具足制禦,內心無垢,純淨安樂。布吒婆樓,比丘如是守護諸根之門。 復次,布吒婆樓,比丘云何具足正念正知?今有比丘,若進若退,悉以正知;直視、周視,悉以正知。若屈伸
手足,若執持衣缽,若飲食咀嚼,若大小便利,若行住坐臥,若覺醒語默,於一切時,悉以正智。布吒婆樓,比丘如是具足正念正知。
復次,布吒婆樓,比丘云何自知滿足?今有比丘,以衣保身,以食養體,自知滿足。任往何處,持與俱行,如有翼鳥,任飛何處,羽翼隨身。此比丘亦復如是,以衣保身,以食養體,自知滿足,任往何處,持與俱行,布吒婆樓,比丘如是自知滿足。
具足如此聖戒聚,聖諸根制禦,聖正念正知,聖滿足比丘,或在靜處,或在樹下,或在山谷,或在巖窟,或在塚間,或在林藪,或在露野地,或在藁堆,離世閑居,彼受施食還,食已,結跏趺座,端身安住於深正念。 彼於世間,棄除貪欲,住無貪欲心,離去貪欲,令心淨化,棄除害心,棄除嗔恚,住不害心,普為利益慈愍一切生類有情。離去害心,離嗔恚,令心淨化。棄除昏沉,棄除睡眠,離去惛睡,繫想分明,正念正知。離去昏睡,令心淨化,棄除掉舉,及以惡作,住心輕安,內心寂靜。離去掉舉,及以惡作,令心淨化,棄除疑惑,住離疑惑,而於淨法無有疑惑。離去疑惑,令心淨化。
10 捨此五蓋,觀自身者,便生歡喜。歡喜者生喜,懷喜者身安穩,身安穩便覺樂,樂則心入三昧。彼離諸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住初禪。因此先滅欲想,是時生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他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彼已離生喜樂,潤漬其身,周遍盈滿,全身到處無不遍滿離生喜樂。因此先滅欲想,是時生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
譬如善巧浴僕,或其弟子,於盥浴器,而撒澡豆,以水漬調,澡豆受潤,因潤散碎,內外俱潤,以至周遍,無不遍滿。比丘亦復如是,離生喜樂,潤澤其身,周遍盈滿,全身到處,無不遍滿離生喜樂。因此先滅欲想,是時生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他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11 世尊復言:「布吒婆樓,復有比丘,滅除尋伺,內心靜安,得心一境相,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入第二禪。是時先滅離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定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定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他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定生喜樂,潤澤其身,周遍盈滿,全身到處,無不遍滿無喜之樂。譬如有水湧出深泉,其水不從東來,不從西來,不從北來,不從南來,而時時予以驟雨。由此深泉湧出涼水,以此涼水,潤漬深泉,周遍盈溢,且復充滿全泉之水,無不普洽。比丘如是,定生喜樂,潤漬其身,周遍盈滿,全身到處,無不遍滿定生喜樂。
12 世尊復言:「布吒婆樓,復有比丘,離喜住捨,正念正知,身受快樂,如諸聖說,『捨念樂住。』入第三禪。是時先滅定生喜樂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捨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捨樂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他想滅,此由於修習也。」譬如青紅白蓮,一一蓮池,是蓮皆生水中,皆長水中,皆浸水中,為水所養,由頂至根,以水潤漬,周遍盈溢,且復充滿,全身到處,無不遍滿無喜之樂。
13 世尊復言:「布吒婆樓,復有比丘,捨樂離苦,先滅憂喜,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入第四禪。是時先滅捨樂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不苦不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不苦不樂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他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譬如有人,由頂至踵,以白淨衣被覆,全身到處惟白淨衣。比丘亦復如是,以純淨心充滿其身,全身到處惟純淨心,周洽普遍。如是心寂靜純淨,無有煩惱,離隨煩惱,柔然將動,恆安住於不動相中,爾時比丘,以心傾注於智見。彼知是事:「我身由色成,四大種成,父母所生,粥飯長養,為無常、破壞、粉碎、斷絕、壞滅之法,又我之識依存於此,與此關聯。」
譬如琉璃寶珠,美麗優雅,八面玲瓏,磨治瑩明,清澄無濁,具一切美相,以索貫之,索深青色,若深黃色,若赤紅色,若純白色,若淡黃色,有目之士,置掌而觀,當如是觀此琉璃之相。比丘如是,心寂靜純淨,…爾時比丘,以心傾注於智見。彼知是事:我身由色成…我之識依存於此,與此關聯。
14 世尊復言:「布吒婆樓,復有比丘,超出所有色想,滅障礙想,不憶異想,故達空是無邊之空無邊處,因此先滅此想,同時生空無處樂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惟有空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他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今有沙門或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此我為有色,四大所成,父母所生,而身壞時,斷滅消失,死後無存。於是此我,全歸斷滅。
復有餘者於此作是說言:「汝言之我,斯我實存,予決不謂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斷滅。猶有他我,是天而有色,屬於欲界,養於段食,汝不知見,予知見之。此我身壞,斷滅消失,死後無存,於是此我,全歸斷滅。 復有餘者於此作是說言:「汝言之我,斯我實存,予決不謂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斷滅,猶有他我,是天而有色,且意所成,肢節具足,諸養無闕,汝不知見,予知見之。此我身壞,斷滅消失,死後無存。於是此我,全歸斷滅。
復有餘者於此作是說言:「汝言之我,斯我實存,予決
不謂,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斷滅。猶有他我,超出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憶異想,故達空是無邊之空無邊處。汝不知見,予知見之。此我身壞,斷滅消失,死後無存。於是此我,全歸斷滅。
15 世尊復言:「布吒婆樓,復有比丘,超出所有空無邊處,達識是無邊之邊處,因此先滅空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無所有處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識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他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16 世尊復言:「布吒婆樓,復有比丘,超出所有識無邊處,達所有皆無之無所有處,因此先滅識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無所有處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有無所有處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他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17 布吒婆樓,以比丘有獨特之想,彼便由前至後,次第以至想之極致,處此想之極致時,彼作是念:「思慮之事,於我為惡;不思慮事,於我為善。設我仍有思慮意欲,我之此想雖得消滅,而餘粗想將復再生。我今寧可不為思慮,不起意欲。」彼便不為思慮,不起意欲。不為思慮不起意欲已,其想即滅,餘想不生,而彼想滅。布吒婆樓,如是次第以至增上想滅智定。
18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汝曾聞如斯次第增上想滅智定否?」否也,世尊,今吾唯知世尊所說,謂:「以比丘有獨特之想,彼便由前至後,次第以至想之極致,處此想之極致時,彼作是念:『思慮之事,於我為惡;不思慮事,於我為善。設我仍有思慮意欲,我之此想雖得消滅,而餘粗想,將復再生。我今寧可不為思慮,不起意欲。』彼便不為思慮,不起意欲。不為思慮不起意欲已,其想即滅,餘想不生,而彼想滅。布吒婆樓,如是次第以增上想滅智定。」布吒婆樓,實如是也。
19 「世尊,世尊說示想之極致,為一為多耶?」,「布吒婆樓,吾所說示想之極致,亦一亦多。」,「如是世尊,云何說示想之極致,亦一亦多耶?」,「布吒婆樓,實如是如是而想滅,遂如是如是現想之極致。布吒婆樓,故吾說示想之極致,亦一亦多。」
20 「世尊,先有想生,然後智生耶?先有智生,然後想生耶?抑智與想非前非後而生耶?」布吒婆樓,先有想生,然後智生;實由想生,而智生起,是以人人皆悉自知:「實由此緣故,於吾生智慧。」布吒婆樓,可知依此理趣,先生想,後生智,由想生故有智生起。
21 「世尊,想即人我耶,抑想與我為異耶?」布吒婆樓,汝以何者為我耶?「世尊,吾自思惟,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養。」布吒婆樓,汝之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養。設若真實,布吒婆樓,則汝想與我,實非一物。布吒婆樓,由此差別智,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吒婆樓,如是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養。但於此人,猶有一想生,他想滅。布吒婆樓,由此差別,可得而知,想我實非一。
22 「世尊,吾以我為意所成,肢節具足,諸根圓滿。」布吒婆樓,汝之我為意之所成。肢節具足,諸根圓滿。設若真實,布吒婆樓,則汝想與我,實非一物。布吒婆樓,由此差別智,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吒婆樓,如是我為意所成,肢節具足,諸根圓滿。但於此人,猶有一想生,他想滅。布吒婆樓,由此差別,可得而知,想我實非一也。
23 「世尊,吾以我為無形,而想所成。」布吒婆樓,汝之我為無形,而想所成。設若真實,布吒婆樓,則汝想與我,實非一物。布吒婆樓,由此差別智,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吒婆樓,如是我為無形,而想所成。但於此人,猶有一想生,他想滅。布吒婆樓,由此差別,可得而知,想我實非一。
24 「復次世尊,人我即為想耶?抑想與我為異耶?斯義吾可得知不?」布吒婆樓,我與想為同一耶?抑想與我為各異耶?汝欲知此,甚難甚難。以汝依他宗見,有他宗信仰,持他宗所期,以他宗之研究為歸,以他宗之行持為旨故。
25 世尊,若吾依他宗見,有他宗信仰,持他宗所期,以他宗之研究為歸,以他宗之行持為旨者,故此想即為人我耶?抑我與想為各異耶?知之甚難,如是世尊。
復欲請問,世界常住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 布吒婆樓,世界常住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此為吾所不記。
如是世尊,此世界無常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世界無常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此為吾所不記。
復次世尊,世界有限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世界有限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此為吾所不記。
復次世尊,世界無限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26 復次世尊,此命與身為一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復次世尊,此命與身各異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27 如是世尊,如來死後存在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如是世尊,如來死後不存在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如是世尊,如來死後亦存在亦不存在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如是世尊,如來死後亦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唯此真實而餘者為虛妄耶?布吒婆樓,此為吾所不記。
28 「世尊,凡此等等,世尊何故判為不記耶?」布吒婆樓,此不與義合,不與法合,非根本梵行,非趣出離,非趣離欲,非趣止滅,非趣寂靜,非趣證悟,非趣正覺,非趣涅槃,是故判為不記。
29 「如是世尊,世尊所記為何?」布吒婆樓,「此是苦」,實吾所記者也。布吒婆樓,「此是苦集」,實吾所記者也。布吒婆樓,「此是苦滅」,實吾所記者也。布吒婆樓,「此是趣苦滅之道」,實吾所記者也。
30 「然世尊所記,為何故耶?」布吒婆樓,此實合義合法,是根本梵行,是趣出離,是趣離欲,是趣止滅,是趣寂靜,是趣證悟,是趣正覺,是趣涅槃,故為吾所記。「誠然世尊,誠然善逝。世尊請便,今正是時。」於是世尊起座而去。
31 世尊去未久,苦行外道等皆向布吒婆樓苦行外道譏誚曰:「布吒婆樓,於沙門瞿曇所說,作如是讚嘆:誠然世尊,誠然善逝。然於「世間常住耶,世界無常耶,「世界無限耶,世界有限耶,命與身為一耶,命與身各異耶,如來死後存在耶,如來死後不存在耶,如來死後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諸問,吾等不見沙門瞿曇確示一法。」布吒婆樓聞是言已,告彼等苦行外道曰:「諸士,世間常住耶乃至如來死後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諸問,吾固不見沙門瞿曇確示一法。但沙門瞿曇所說之道,如實真正,真如,住法合法,沙門瞿曇,如是善說,如實真正,真如,住法合法之道時,理智如吾者,何由不讚嘆此善說法者耶?
32 後二三日,象首舍利弗與布吒婆樓詣世尊所,象首舍利弗禮敬世尊,坐於一面,布吒婆樓亦親禮世尊,慇勤問訊,就一面坐。布吒婆樓白世尊言:「世尊,世尊去未久,苦行外道等,皆向吾作譏誚曰:『布吒婆樓,於沙門瞿曇所說,作如是讚嘆:誠然世尊,誠然善逝。然於世間常住耶,乃至如來死後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諸問,吾等不見沙門瞿曇確示一法。』世尊,吾聞是言已,答彼等苦行外道曰:『諸士,世間常住耶,乃至如來死後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諸問,吾固不見沙門瞿曇確示一法。然沙門瞿曇所說之道,如實真正,真如,住法合法,沙門瞿曇,如是善說如實真正真如,住法合法之道時,理智如吾者,何由不讚嘆此善說法者耶。』」
33 布吒婆樓,彼等一切苦行外道,皆悉盲目,為無眼子,而於其中,唯汝一人具眼士也。布吒婆樓,我所說法,有決定記,不決定記。布吒婆樓,云何名為我所說法不決定記?蓋謂「世界常住耶」者是也,布吒婆樓,此為我所說法,不決定記。復次,布吒婆樓謂「世界無常耶」者是也,此為我所說法,不決定記。布吒婆樓,謂「世界有限耶,乃至如來死後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者是也,此亦為我所說法,不決定記。
布吒婆樓,何故此等為我所說法,不決定記?布吒婆樓,以此等不與義合,不與法合,非根本梵行,非趣出離,乃至非趣涅槃故也,是故此等為我所說法,不決定記。
布吒婆樓,云何名為我所說法之決定記?布吒婆樓,「此是苦」,實為我所說法之決定記。布吒婆樓,「此是苦集」,實為我所說法之決定記。布吒婆樓,「此是苦滅」,實為我所說法之決定記。布吒婆樓,「此是趣苦滅之道」,實為我所說法之決定記。
布吒婆樓,何故此等為我所說法之決定記。布吒婆樓,以此等與義合,與法合,是根本梵行,是趣出離,乃至是趣涅槃故也。是故此等,為我所說法之決定記。
34 布吒婆樓,或有一類沙門婆羅門,謂「我於死後,一向安樂,亦無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見。我訪彼等,如是問曰:「諸友,汝等謂我於死後,一向安樂,亦且無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見,真實不耶?」彼等聞是言,報我曰:「然。」我又問曰:「諸友一安樂之世界,汝等實知實見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不也。」我又問曰:「諸友,汝等於一夜或一日,於半夜或半日,亦曾審知有一向安樂之我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不也。」我又問曰:「諸友,趨於一向安樂世界,惟此道可實現,惟此路得通達。汝等曾了知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不也。」我又問曰:「諸友,生彼世界一向安樂安樂之天神曰:『尊主若欲實現一向安樂世間,當行善業,當行正道,當步正道,所以者何?吾等所行正爾,故得生於一向安樂世界。』汝等曾聞其說示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不也。」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彼等沙門婆羅門所說,合正理否?
35 譬如有人,作如是言:「吾於此國中,求交且愛第一美女。」餘人若問:「吾友,汝於此國中,求交且愛第一美女,則汝當知,國中所謂第一美女,屬剎帝利族耶,婆羅門族耶,吠舍耶,抑首陀羅耶。」彼聞是言,答曰:「不知。」
又問彼曰:「吾友,汝於國中,求交且愛第一美女,則汝當知,在此國中,第一美女,名何姓何,彼女身軀,長耶短耶?適中耶?彼女皮膚,青黑耶?純黑耶?黃金色耶?彼女所住,村落鄉鎮耶?抑城市耶?」彼聞是問,答曰:「不知。」
又問彼曰:「吾友,汝求交且愛者,汝竟不知其人,不見其人耶!」彼聞是問,答曰:「唯然。」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此人所說,合正理不?世尊,此人所說,實不合正理也。
36 布吒婆樓,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謂「我於死後,一向安樂,亦且無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見。我訪彼等,如是問曰:「諸友,汝等謂我死後,一向安樂,亦且無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見,真實不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不也。」
我又問曰:「諸友,汝等於一夜或一日,於半夜或半日,亦曾審知一向安樂之我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唯然。」
我又問曰:「諸友,趨於一向安樂世界,惟此道可實現,惟此路得通達。汝等曾了知耶?」彼等聞是問,答我言:「不也。」
我又問曰:「諸友,生彼世界一向安樂之天神曰:『尊主,若實現一向安樂世界,當行善業,當行正道,所以者何?吾等行此,故得生於一向安樂世界。』汝等曾聞其說示耶?」彼聞是問,答我言:「不也。」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此人所說,合正理不?世尊,此等沙門婆羅門所說,實不合正理也。
37 布吒婆樓,例如有人,於四衢道處,欲樹立一梯,以登殿堂,餘人問彼曰:「今者吾君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在東方耶?在西方耶?在北方耶?抑南方耶?其堂高耶?低耶?抑適中耶?君知之耶?」彼於此問答曰:「不知。」
餘人又問:「今者吾友,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君竟不知不見耶?」彼於此問,答曰:「唯然。」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此人所說,合正理否?世尊,此人所說,實不合正理也。
38 布吒婆樓,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謂「我於死後,一向安樂,亦且無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見。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彼等沙門婆羅門所說,合正理否?世尊,彼等沙門婆羅門所說,實不合正理也。
39 布吒婆樓,實有三種我得,即粗我得,意所成我得,無形我得。布吒婆樓,何者是粗我得耶?有形而四大所成,段食所養者,粗我得也。何者是意所成我得耶?有形而肢節具足,諸根圓滿者,意所成我得也。何者是無形我得耶?無形之想所成者,無形我得也。
40 布吒婆樓,我之說法,實欲使永斷粗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自身證達,至於安住。布吒婆樓,汝意或謂:「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欲自證達,至於安住,然而有情猶住苦中。」
布吒婆樓,勿作是念,所以者何,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能自證達,而自安住,是則愉悅歡喜,成就輕安,又得正念正知,住於安樂。
41 布吒婆樓,我之說法,實為欲使永斷意所成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自身證達,至於安住。
布吒婆樓,汝意或謂:「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欲自證達,至於安住,然而有情猶住苦中。」
布吒婆樓,勿作是念,所以者何,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能自證達,而自安住,是則愉悅歡喜,成就輕安,又得正念正知,住於安樂。
42 布吒婆樓,我之說法,實欲使永斷無形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
43 布吒婆樓,又若有人,向我問曰:「尊者,汝之說法,云何永斷粗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耶?」於如是問,我當答曰:「吾友,我之說法,如是欲使永斷粗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
44 布吒婆樓,又若有人,向我問曰:「尊者,汝之說法,云何永斷意所成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耶?」於如是問,我當答曰:「吾友,我之說法,如是欲使永斷意所成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
45 布吒婆樓,又若有人,向我問曰:「尊者,汝之說法,云何永斷無形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耶?」於如是問,我當答曰:「吾友,我之說法,如是欲使永斷無形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我之所說,合正理不?世尊,世尊所說,實合正理也。
46 布吒婆樓,猶如樹立一梯於殿堂下,欲登一殿堂,餘人問彼曰:「今者吾友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在東方耶?在西方耶?在南方耶?抑北方耶?高耶?低耶?抑適中耶?君知之耶?」彼答問言:「我之立梯於殿堂下,為欲如是以登殿堂。」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此人所說合正理否?世尊,彼之所說,實合正理也。
47 布吒婆樓,此亦如是,設若有人,向我問言:「尊者,汝之說法,云何永斷粗我得?復次,汝之說法,云何永斷意所成我得云云?復次,汝之說法,云何永斷無形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於現法中,智慧充廣,自身證達,至安住耶?」於如是我當答曰:「吾友,我之說法,如是永斷無形我得,依之隨入,斷離染汙法,增長清淨法,如是乃至住於安樂。」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我之所說,合正理不?世尊,世尊所說,實合正理也。
48 時象首舍利弗白世尊言:世尊,粗我得存在時,意所成我得之存在為虛,而無形我得之存在亦虛。正於爾時,唯粗我得之存在為實耶?
世尊,意所成我得存在時,粗我得之存在為虛,而無
形我得之存在亦虛。正於爾時,唯意所成我得之存在
為實耶 ?
世尊,無形我得存在時,粗我得之存在為虛,而意所成
我得之存在亦虛。正於爾時,唯無形我得之存在為實耶?
49 象首,粗我得存在時,唯名為粗我得,決不名為意所成我得,亦不名為無形我得。
象首,意所成我得存在時,唯名為意所成我得,決不名粗我得,亦不名為無形我得。
象首,無形我得存在時,唯名為無形我得,決不名粗我得,亦不名為意所成我得。
象首,設若有人向汝問言:「汝曾存於過去世,汝非已有耶?汝將存於未來世,汝非當有耶?汝存於現在,汝非今有耶?」象首,有是問者,汝云何答?
世尊,設若有人,向我問言:「汝曾存於過去世,汝非已有耶?汝將存於未來世,汝非當有耶?汝存於現在,汝非今有耶?」世尊,有是問者,我當答言:「我曾存於過去世,我曾已有;我將存於未來世,我為當有;我存於現在,我為今有。」世尊,於如是問者,我當如是答。
50 象首,又若問汝:「汝有過去我得時,唯汝之此我得為實,而未來我得為虛,現在我得亦為虛耶?復次,汝有未來我得時,唯汝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我得為虛,現在我得亦虛耶?復次,汝有現在我得時,唯汝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我得為虛,未來我得亦虛耶?」象首,有是問者,汝云何答?
世尊,若問我言,「汝有過去我得時,如是乃至汝有現在我得時,唯汝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者為虛,未來者亦虛耶?」
世尊,有是問者,我當答言:「有過去我得時,唯我之此我得為實,而未來者為虛,現在者亦虛也。復次,我有未來我得時,唯我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者為虛,現在者亦虛也。復次,我有現在我得時,唯我之此我得為實,而過去者為虛,未來者亦虛也。」於如是問者,我當如是答。
51 象首,此亦如是,粗我得存時,決不名為意所成我得,亦不名為無形我得,唯名為粗我得也。象首,意所成我得存時,乃至象首,無形我得存時,決不名為粗我得,亦不名為意所成我得,唯名為無形我得也。
52 象首,譬如由牛有乳,乳變為酪,酪為生酥,生酥為熟酥,熟酥為醍醐,當有乳時,唯名為乳,決不名酪,不名生酥,不名熟酥,不名醍醐。當有酪時,乃至有酥時,乃至有醍醐時,唯名醍醐,決不名乳,亦不名酪,不名生酥,不名熟酥。
53 象首,此亦如是,粗我得存時,乃至意所成我得存時,乃至無形我得存時,決不名為粗我得,亦不名為意所成我得,唯名為無形我得也。象首,凡此等等,為世間共相,世間言語,世間名稱,世間記述法,如來用之,正當者也。
54 世尊如是說已,布吒婆樓苦行外道曰:「偉哉世尊,大哉世尊,猶如使倒者得起,閉者得開,迷途者示之以道,冥室燃燈,有目得視。世尊以無數方便,說示教法,亦復如是。世尊,我今歸依佛陀,歸依法,歸依僧眾。唯願世尊,聽攝受我,自今已後,盡壽歸依,為優婆塞。」
55 象首舍利弗白世尊言:「偉哉世尊,大哉世尊,猶如使倒者得起,閉者得開,迷途者示之以道。冥室燃燈,有目得視。世尊以無數方便,說示教法,亦復如是。世尊,我今歸依佛陀,歸依法,歸依僧眾。唯願世尊,許我等於世尊所,得出家受具戒。」
56 於是,象首舍利弗,於世尊處,出家受具戒,受具戒後,尊者象首舍利弗,即獨處,不放逸,慇勤專念,精勤止住。為良家子出家所求最上梵行之究竟道,彼為時未久,即於現在,自身作證,自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尊者象首舍利弗,成阿羅漢。
修習慈心
(Metta Bhavana)
1. 願我無怨,無瞋,無憂,
願我守護自己,住於安樂。
2. 願我的父母、師長、親人、同參道友,無怨, 無瞋,無憂,願他們守護自己,住於安樂。
3. 願在此寺的所有禪修者,無怨,無瞋,無憂,
願他們守護自己,住於安樂。
4. 願在此寺的所有比丘、沙彌、優婆塞和優婆夷,
無怨,無瞋,無憂,願他們守護自己,住於安樂。
5. 願四事護法眾 ,無怨,無瞋,無憂,
願他們守護自己,住於安樂。
6. 願此精舍,此居所,此寺院的護法諸天,無怨,
無瞋,無憂,願他們守護自己,住於安樂。
7. 願一切有情眾生,無怨,無瞋,無憂,
願他們守護自己,住於安樂。
作者簡介
作者艾雅.柯瑪(Ayya Khama)於1923年生於德國的猶太家庭。1938年與其他兩百位兒童逃離德國,被送往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她的父母親則到了中國。兩年後,艾雅.柯瑪到上海與父母團聚。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全家被關在日本人的戰犯營,父親在獄中去世。
之後,美國解放了戰犯營,四年後,艾雅.柯瑪移民美國,並育有子女各一,現在則有四個孫子。艾雅.柯瑪於1960年至1964年間,與夫婿和兒子四處遊歷,足跡遍及喜瑪拉雅山區的國度,而這是她第一次接觸禪修。十年後,艾雅.柯瑪開始在歐洲、美國及澳洲教導禪修。
1978年,艾雅.柯瑪在澳洲.雪梨附近成立了上座部森林道場。1979年在斯里蘭卡,作者由大長老那羅達(Narada Mahathera)親證剃度出家,法名為Khema,意為安穩;Ayya是值得尊敬的意思。在斯里蘭卡的首都可倫坡,艾雅.柯瑪成立了國際佛教徒婦女中心(International Buddhist Women’s Center),做為斯里蘭卡出家女眾的訓練中心。另外還有專為女眾閉關或剃度的尼眾島嶼(Parappuduwa Nuns’ Island)。
1987年,艾雅.柯瑪舉辦佛教史上第一屆的國際佛教尼眾會議,由達賴喇嘛擔任主題演講人。並成立一個世界性的佛教婦女組織-釋迦兒女(Sakyadhita)。同年五月,成為第一位受邀到聯合國發表有關佛教議題的演講人。於1989年創立的德國Buddhist –Haus佛教團體,奉她為精神導師。1997年六月,艾雅.柯瑪創立了德國的第一座佛教森林道場-慈心精舍(Metta Vihara),並第一次在此以德語舉行剃度典禮。1997年十一月二日,艾雅.柯瑪在德國圓寂。
艾雅.柯瑪寫了二十五本以上有關禪修和佛教教理的書,並以英文和德文弘揚佛法,她的作品被翻譯成七種語言,包括《緣起性空的世界》、《堅若磐石》、《何來有我》、《把我的一生獻給你》等書。
願以此法施功德,滅盡諸煩惱;
願以此法施功德,成為涅槃因;
願以此法施功德,與眾生分享。
願 一切眾生安樂(慈),
願 幫助眾生離苦(悲),
願 樂見眾生成就(喜),
願 待人冤親平等(捨)。
譯者:果儒
校對:慈迦、何彩熙
流通處:
◎慈善精舍(果道法師)
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37巷17弄9號5樓
電話:(02)2648-6948
◎中平精舍(果儒法師)
32444桃園縣平鎮市新榮路71號(新勢國小旁)
◎ 法雨道場(明德法師)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柚仔宅50~6號
電話:(05)2530029
◎ 耿欣印刷有限公司
(02)2225-4005
初版:西元2010年5月 恭印3,000本